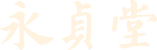宋代道学话语的形成,是众多社会文化思潮互动的结果。在道学话语创立的过程中,二程(程颢、程颐)的思想魅力和人格感召起了关键的作用,朱熹则以其博学多识和精密论证把道学思潮和话语推向了一个高峰。在不同学派、不同思潮的相互交锋中,道学话语也在不断走向丰富和完善,并随着时代主题和思考模式的变化而变化。本文认为,“定性”是宋代道学的一个重要话题,“定性”学说关涉到性为何物、性之内外、性与情、性与心、性与仁义、性与理、性与事(物)、存养工夫等道学核心话语;因此,探讨这一话语系统的形成、发展与转折,是研究早期道学史的要害所在。
一、明道《定性书》:“定性”话语的提出
“定性说”最早见于《二程文集》程颢《答横渠先生定性书》。其中,面对张载“定性未能不动,犹累于外物”的疑惑,明道(程颢亦称明道先生)的答书即成就了道学思想史上著名的《定性书》。《定性书》率先提出了道学“定性”话语,它由性与情、性与心、动与静、定的功夫等话语片断组成一个话语系统。在《定性书》中,明道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性无内外”说和“内外两忘”的定性方法论。
张载的困惑主要在于如何排除外物的干扰,求得内心的宁静。而明道的回答主要落实在“定”上:由定而静,由定而达到“内外之两忘”,由定而达到“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的精神境界。牟宗三先生指出,“张横渠所说的是消极工夫上的问题,是就心之为感性所制约而说。明道之答复是积极工夫上的问题,是就本心性体之自身而说。”(牟宗三,第236页)在明道这里,“定性”最初为一种存养工夫,它的完成能进入一个崇高的精神境界。明道指出:
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苟以外物为外,牵己而从之,是以己性为有内外也。且以性为随物于外,则当其在外时,何者为在内?是有意于绝外诱,而不知性之无内外也。既以内外为二本,则又乌可遽语定哉?(《定性书》)
所谓“定”,并不是指内心寂然不动,更不是指对外物不作任何反映。“定”指心性本体的贞定:心性本体无动静,无内外;不能以静为定,而以动为不定。如果我们以外物为外,那么我们接应外物的时候,难道不就是牵己以随物、随物而动,把自己的本性置之于外了吗?如果本性随外物而动,那么什么又是我们内在的本性呢?我们有意识地排除外物的诱惑,实质上就是以性为外而非内。反之,我们如果以性为内,那么我们又如何去感应外物呢?因此,将性置于内或置于外,都无法做到真正的“定性”;正确的看法应是内外贯通为一,即“性无内外”。只要真正彻悟“性无内外”,内心也就不会随物而动,受到外物的干扰了。既然“性无动静”、“性无内外”,“定性”也就不是针对“性体”自身而言,“定性”所“定”的就是“性之表现”时之心定。(参见牟宗三,第235页)牟先生是基于他的心学立场得出这一结论的,他的理解值得我们深思。在道学初期,明道、张载对“性”的理解固然有所不同,但没有“性体”这一认识,而如果“性”不能定,那么“定性”话语也失去了其存在的前提和依据。其实,把握“定性”说,对于“性”的理解是关键。明道、张载都以“气”论“性”:气禀有善恶,固性有善恶,“定性”就是要使性“定”于至善之性上,心定只是定性之后的外在表现而已。这一点朱子讲得最清楚,朱子对“定性”说的发展也体现在对“性”的理解的深入上。故《定性书》虽以“定性”明篇,而实义则是“定心”。(参见蔡仁厚,第340页)
明道的定性方法主张“内外两忘”,其核心在于排除自私、用智对人心的蒙蔽,提升自我精神境界:
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则不能以有为为应迹,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今以恶外物之心,而求照无物之地,是反鉴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孟氏亦曰:“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与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两忘也。两忘则澄然无事矣。无事则定,定则明,明则尚何应物之为累哉?(《定性书》)
要使人心不受外物的困扰,必须解除自私、用智的心患。自私是私心,是有我,是内;用智是算计,是有物,是外。由于人们的自私、用智,因而永远无法达到“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的“定”境。这就好比明镜原本虚明,无心无情,不送不迎,物来顺应,可是由于我们有了厌恶外物的私心(自私),挖空心思把镜子反过来照于无物之地(用智),结果当然什么也看不到。明道十分推崇艮卦“止其所当止”的精神,认为,在艮卦卦辞中,“艮其背,不获其身”就是无我,是忘内;“行其庭,不见其人”就是无人,是忘外,它们真正体现了其“定性”理论的真精神——“内外之两忘”的精神。简言之,自私和用智把世界一分为二,世界分割成内和外、我与非我,二者之间不能统一,自然妨碍了我们求道之心,使我们无法摆脱内在欲望和外在诱惑的困扰。因此,只有做到内外两忘,才能澄然无事,澄然无事则能内心贞定,内心贞定则天人合一、一片澄明,内心又怎么还会受到外物的困扰呢?
“定性”的境界,明道称之为“天地”之境、“圣人”之境。他说:
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同上)
“天地”之境即“无心”之境:天地能泽润万物,以生物为心,没有任何私意,天地“廓然而大公”,故“无心”。“圣人”之境即“无情”之境:圣人之情,顺应万物而不私偏,没有任何个人私情在内,圣人“物来则顺应”,故“无情”。君子之学,关键在于学习“天地”之“无心”和圣人”之“无情”,即消除个人的私心私欲,消解个我的情感意志,达到“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的“定”境;它实质上就是明道反复倡明的“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二程遗书》卷二上)的自然和乐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因此,“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朱子语类》卷九五)既是《定性书》的纲领,也是明道定性说的理论归宿。
定性话语一旦奠定,《定性书》即成为了理学经典文献,被收入《近思录》(南宋朱熹、吕祖谦编)、《理学要旨》(清代耿介编)、《性理纂要》(清代冉觐祖编)等书,在宋明思想史上影响深远。后世道学家或心学家都从中吸取营养,阐发自己的道学或心学。在心学方面,明代何祥尝阅性理,得明道先生《识仁论》、《定性书》,好之不忘,遂为批注,著有《识仁定性注解二卷》。《四库提要》称:“祥之学出于姚江,此书所论皆发明心学。”(《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六)明代刘宗周的《圣学宗要》一书,载有周子《太极图说》、张子《东铭》《西铭》、程子《识仁说》《定性书》、朱子《中和说》、王守仁《良知问答》等篇,各为注释。(参见同上,卷九三)在道学方面,仅南宋就有朱熹、叶采叶采在他的《近思录集解》卷二中对明道的《定性书》逐条作注。叶采为朱子的再传弟子,其思想上接朱子。、真德秀等对明道《定性书》作注,且多有创发,极大地丰富了明道定性学说的理论内涵。
二、朱子“定性说”:“定性”话语的展开
“定性”话语的展开与朱熹的深切关注密不可分。朱子非常重视明道的《定性书》,他称赞此书“自胸中泻出,如有物在后面逼逐他相似,皆写不辨”,认为“明道言语甚圆转,初读未晓得,都没理会。仔细看,却成段相应,此书在鄠时作,年甚少”(《朱子语类》卷九五);并认定《定性书》“直是条理不乱”(《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二),“中间自有脉络贯串将去”(《朱子语类》卷九五)。朱子认为,《定性书》不仅逻辑缜密、思想深刻,而且还体现了明道从容、和乐、谦和、洒脱的“圣人气象”胡安国曾对《定性书》进行删节,删除书信开头及结尾的客套话数十字。朱子认为,胡文定改削《定性书》,虽无损义理,但有损明道的“圣人气象”(参见《与刘共父》,《朱文公文集》卷三七)。。朱子与众弟子广泛讨论《定性书》,朱子与弟子有关《定性书》的问答详见《朱子语类》,其中,卷九五载有十五条,卷七三、九三各有一条。清代江永《近思录集注》皆有收录。并作《定性书解》据《晦庵集》别集卷二载,朱子在给程允夫的书信中称:“《近思》已成,尚未寄到,到即附去。《中庸》无人写得,只有一本,不敢远寄,且亦未定,不欲广传也。《定性书解》在别纸,亦勿示人为佳。《云谷记》已写,寄李文矣。”可见《定性书解》与《近思录》同时成书。考之《朱子年谱》,《近思录》成书于淳熙二年,也就是说,公元1175年《定性书解》已成书,可惜今已佚失。、《定性说》,进一步阐发了明道的“定性”学说。
从字面的意义上看,“定性”存在两种不同的解释向度:注重“定性”之“定”容易走向工夫论,注重“定性”之“性”则容易滑向效果论。与明道强调“定”(性)的致思路向不同,朱子的思想路径侧重于“性”(定),他说:
定性者,存养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则动静如一,而内外无间矣!天地之所以为天地,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学,亦以求定而已矣。(《定性说》,《朱文公文集》卷六七)
明道的《定性书》主要立足于性如何“定”,侧重于存养工夫和修养的方法、过程;而朱子则重视“性”定之后的效果,认为存养工夫的完成就得到了“性之本然”——性的本体,它是纯粹至善的。达到“性之本然”的状态,朱子称之为“性定”。很显然,朱子十分赞同明道的“性无内外”说,但他们各自的路径不同。朱子认为,天地之所以成为天地,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关键就在于他们能做到动静如一、内外无间,而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就是“仁立义行”:
故廓然大公者,仁之所以为体也。物来顺应者,义之所以为用也。仁立义行则性定,而天下之动一矣!(同上)
应该注意到,朱子的“性之本体”,“便是仁义礼智之实”(《答林德久》,《朱文公文集》卷六一),“仁、义、礼、智,性也”(《孟子集注》卷三)。而在仁义礼智四德之中,仁又是最根本的,它可以派生和包摄后三者。义是宜,是裁断;仁是体,是所以然;义是用,是所当然。仁义可以包含礼智:“四端犹四徳,逐一言之,则各自为界限;分而言之,则仁义又是一大界限”,“直卿云,六经中专言仁者包四端也。言仁义而不言礼智者,仁包礼,义包智”(《朱子语类》卷六)。换言之,“仁义”就是“性之本体”,“求仁行义”就能“性定”。这样,以“求定”为目标的君子之学便转化为“求仁行义”之学。做到了这一点,也就达到了明道孜孜以求的“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的“定”境。
然而,朱子所谓的“性之本体”就是“理”,“性之本体,理而已矣”(《四书或问》卷三六)。他所谓的“仁义”也不过是“天理”的自然显现。“仁义,天理之自然也。居仁由义,循天理而不得不然者也”(同上,卷二六)。因而“定性”所得到的“性之本然”——性的本体,即是宇宙的终极本体——理。一旦豁然贯通,穷尽天理,“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大学章句》)。因此,“内外两忘”和“定性”最终都必须依理而动,“一循于理”:
内外两忘,非忘也,一循于理。不是内而非外也,不是内而非外,则大公而顺应,尚何事物之为累哉?圣人之喜怒,大公而顺应,天理之极也。众人之喜怒,自私而用智,人欲之盛也。忘怒则公,观理则顺,二者所以为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定性说》,《朱文公文集》卷六七)
“内外两忘”并非真的忘记,而是随理顺应,以理为标准,大公无私,真正摆脱了万物的纷扰。大凡常人的喜怒哀乐都会受到外物的困扰,在物欲的诱惑面前摆脱不了自私和用智;而圣人的喜怒哀乐,则大公无私,物来顺应,体现了天理的极致。也只有真正做到忘记愤怒,以理观物,才能达到“大公而顺应”的“定”境。然而,达到“大公而顺应”的“定”境,必须通过向内探求即通过“自反”来获得。朱子在回答弟子的疑问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先生举人情易发而难制者,惟怒为甚,惟能于怒时遽忘其怒,而观理之是非。旧时谓观理之是非才见己是而人非,则其争愈力。后来看不如此,如孟子所谓我必不仁也,其自反而仁矣。其横逆由是也,则曰:此亦妄人而已矣。(《朱子语类》卷九五)
“观理之是非”并不是要求证“己是而人非”,而是反求诸己,“自反而仁”,通过向内探求,揭示出内心早已存在的“天理”。理就在心中,只有通过心的自觉活动才能彰显。“大抵理只是此理,不在外求,若于外复有一理时,却难为只有此理故。”(同上)
也许正是因为强调“自反”的定性途径,朱子在回答舜弼问《定性书》很难理解时说:“也不难,定性字说得也诧异,此‘性’字是个‘心’字意。”(同上)把“性”理解为“心”在朱子哲学里并不多见。这里的“心”与心学作为本体的“心”有根本的不同,它“只是一个现实的、经验意识的概念,只是一个感应知觉之心,在经验意识和现实知觉之外不存在其他作为本体的心,在变化出入的心之外不存在其他不起不灭的心”(陈来,2000年,第249页)。至于如何认识“心”,朱子的高足黄勉斋也说:“此书(按:指《定性书》)分七段,读此首段定性字当作定心看,若以心有内外不惟未可语定,亦且不识心矣。”(江永撰《近思录集注》卷二)由于“心”无内外,故性无内外,性无内外则不为外物所诱惑,从而实现内心的宁静,这一思想是对明道《定性书》的进一步发挥。在《定性书》里,明道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定性即是定心,但他在回答持国的问题时有一段话值得玩味:
持国曰:“道家有三住,心住则气住,气住则神住。此所谓存三守一。”伯淳先生曰:“此三者,人终食之顷未有不离者,其要只在收放心。”(《二程遗书》卷一)
明道认为,保持心、气、神的安定,不受外物的干扰,关键在于“收放心”。在《二程遗书》中,二程在回答弟子问如何屏去思虑纷乱、保持内心的宁静时,其所说如“(心)中有主”(《二程遗书》卷一)、“持其志”(同上)、“要作得心主定”(同上,卷十五)、“要立个心”(同上)、“唯是心有主”(同上),都是从“心”上去落实。《二程遗书》诸多的问答也启示我们,张载“定性未能不动,犹累于外物”的疑惑在道学初期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话语,而明道《定性书》的深刻解答极具典范意义。
三、西山“定性论”:“定性”话语的烂熟与转折
真德秀(1178—1235年),人称“西山先生”。西山早年曾师从朱子弟子詹体仁,为朱子的再传弟子,是南宋嘉定(1208—1224年)以后继承朱子学的杰出代表。全祖望称:“乾淳诸老之后,百口交推,以为正学大宗者,莫如西山。”(《西山真氏学案》,《宋元学案》卷八十一)西山私淑朱子,但其为学宗旨却推崇有心学倾向的程明道。他撰写《程明道先生书堂记》,自述从小诵习明道之书,长而愈见佩服,以为可以开千古之秘,而觉万世之迷。而对于朱子,却很少见到西山此类的话语。(参见甲凯,第3513页)遵循明道和朱子的学术理路,西山曾对《定性书》作注,并从本体论的高度阐发了他对“定性”的见解,提出了“理定于中”、“理即事,事即理”两个重要命题。他说:
定性者,理定于中而事不能惑也。理定于中,则当静之时固定也,动之时亦未尝不定也。不随物而往,不先物而动,故曰:无将迎。理自内出而周于事,事自外来而应以理,理即事也,事即理也。故曰:无内外。(《西山读书记》卷二)
西山认为,“定性”的本质就是“理定于中”,“理定于中”则万事万物无法迷惑我们的心智。西山预设的理论前提是程朱一贯主张的“性即理”,他论证的主要思路是:理无动静性无动静;理无内外性无内外。西山认为,“天理”就驻守在我们心中,意识到心有所主,我们就能动亦定,静亦定,不会受到外物的影响,不会先物而动,这就是明道的“无将迎”。理在心中,从心内流出能遍及万事万物;面对万事万物纷至沓来,内心世界一片从容,自然以理接应,理在事中,事在理中,一片自然和乐的景象,这就是明道所谓的“无内外”。
西山进一步指出:“夫能定能应、有寂有感者,皆心之妙也。所以然者,性也。若以定与寂为是,而应与感为非,则是以性为有内外也。事物之来,以理应之,犹鉴悬于此而形不能遁也。鉴未尝随物而照,性其可谓随物而在外乎?故事物未接,如鉴之本空者,性也。事物既接,如鉴之有形者,亦性也。内外曷尝有二本哉?”(同上)人心能定能应、有寂有感,性则是事物所以然之理,心无内外故性无内外。这好比明镜照物,与事物没有接触时,明镜里空无一物,这正是明镜的本性;当明镜与事物接触时,镜中显示出事物的形象,这也是明镜的本性(如明镜不能照物,明镜也失去了明镜的本性)。明镜的本性就是明镜的本性,并没有内外之别。知道了这一点(性无内外),我们的心性就能不为外物所动,始终保持内心的平和与贞定。
那么,如何理解西山的“理即事,事即理”呢?西山继承和发挥了朱熹的体用说,对理与事(物)、道与器、心与物等等,都喜欢以体用关系来解释。在西山的思想世界中,“理即事,事即理”首先指形而上的理与形而下的事物之间的不即不离的关系:“形而上者理也,形而下者物也。有是理故有是物,有是物则具是理,二者未尝相离也。方其未有物也,若可谓无矣,而理已具焉,其得谓之无邪?”(《大学衍义》卷一三)有时候,他也指道在器中,理在物中:“道者,理也;器者,物也。精粗之辨固不同矣,然理未尝离乎物之中。”(同上,卷五)当然,在本质上,“理即事,事即理”指的是理与事(物)之间的体用关系。西山认为:
大抵理之于事,元非二物。异端言理不及事,其蔽为无用;俗吏言事而不及理,其蔽为无本。惟圣贤之学,则以理为事之本,事为理之用,二者相须,本无二致,此所以为无蔽也。(《讲筵卷子十一月八日》,《西山文集》卷十八)
在这里,西山批判了佛老(异端)脱离事物空言道理,最后陷入空疏无用;而一般的官吏又仅言事实而忽视大道,最终游于无根之谈。只有圣贤之学,以理为本、以事为用,理在事中、事在理中,二者不即不离,所以完美无缺。值得一提的是,西山把人与事都纳入物的范畴,特别强调“盈天地之间莫非物也。人亦物也,事亦物也,有是物即具是理。”(《大学衍义》卷五)可见西山“理即事,事即理”的思想,是对程颐“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周易程氏传·易传序》)和朱子“理者物之体”(《朱子语类》卷九八)的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虽然西山主张理与事(物)“未尝相离”,可是,他所谓的“理”又是与程颐、朱子所言一样的先于事物而存在的“实理”、“天理”,因而西山遵循的仍然是与程、朱一致的哲学理路。
虽然西山在《定性书》注解中没有明确提出自己的定性方法论,但是从西山的论著中,我们可以发现他非常重视“以道养心”、“以理养心”:
然则何以宁其志?曰:道而已。道者,人心之正理。以道养心,则物欲不作。而恬愉安平,是谓之宁。(《大学衍义》卷三一)
(远古)动息皆有所养,今皆废此,独有理义之养心耳。(同上,卷三十)
盖穷理以此心为主,必须敬以自持,使心有主宰,无私意邪念之纷扰,然后有以为穷理之基本。心既有所主宰矣,又须事事物物各穷其理,然后能致尽心之功。欲穷理而不知持敬以养心,则思虑纷纭,精神昏乱,于义理必无所得知。以养心矣而不知穷理,则此心虽清明虚静,又只是个空荡荡的物事,而无许多义理以为之主,其于应事接物,必不能皆当,释氏禅学正是如此。(《问学问思辨乃穷理工夫》,《西山文集》卷三十)
西山非常注重义理对人心的主宰作用,认为,只有一切以理为主宰,循理而动,才能排除私意邪念的纷扰,达到内心的恬静安宁。在养心的过程中,“主一”和“持敬”的工夫十分必要。“所谓主一者,静时要一,动时亦要一。平居暇日,未有作为,此心亦要主于一,此是静时敬。应事接物有所作为,此心亦要主于一,此是动时敬。静时能敬,则无思虑纷纭之患;动时能敬,则无举措烦扰之患。如此,则本心常存而不失。为学之要,莫先于此。”(《问敬字》,《西山文集》卷三一)“主一”就是专心于一处,没有任何私心杂念;它能使人心不受外部事物的引诱和影响,是为学的要务。“主一”就是“敬”,通过“主一”就能达到“静时能敬”、“动时能敬”,排除外物干扰的效果。在西山看来,仅有“养心”而不知道“穷理”还远远不够。通过“主一”和“持敬”的工夫来“养心”,也许能做到内心的清明虚静。但内心空荡荡时,如果没有义理为之作主,人心应接事物就并非都能合乎天理,反而有流于禅学的危险。因此,要随时随地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义理的修养和践履上:“义理上进得一分,则物欲上减得一分。真积力久,纯乎义理,则物欲自然消尽。”(《得圣语申后省状》,《西山文集》卷五)认识到纯粹的天理,则物欲自然消失殆尽,万事万物都不能扰乱我的心性,虽然世界酬酢万变,我依然能保持内心的贞定。
西山的“理定于中”、“以道养心”、“以理养心”的思想,强调“理”的纯化和“理”的至上性,把道学“定性说”推向了极致。因此,“定性”话语的发展要取得新的突破,必须寻找新的路径。其实,在朱子那里,当他把“定性”理解为“定心”时,已为“定性”话语进入心学领域预留了空间。尽管朱子极力反对把“心”理解为本体之心,可这正是心学家所孜孜不倦的目标。面对“本心”如何摆脱外物的纷扰,心学的创始人陆象山开出了“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语录》下,《象山集》卷三五)的药方。他坚信,“明得此理,即是主宰,真能为主,则外物不能移,邪说不能惑”。(《与曾宅之》,《象山集》卷一)也就是说,只有真正树立主体的内在自觉,让本心良心成为意识的主宰,任何邪说外诱才不会动摇心志。象山的得意门生杨慈湖则认为,人们思虑纷乱和一切过错都起源于“意”,故要消除这些过失,实现内心世界的安宁、贞定,关键在于“不起意”。“不起意非谓都不理事,凡作事只要合理,若起私意则不可。”(《论中庸》,《慈湖遗书》卷十三)“定无用学,但不起意,自然静定。”(《慈湖学案》,《宋元学案》卷七四)杨慈湖认为,“不起意”是比“定”更高的层次。所谓“不起意”,就是消除任何私心杂念,令本心自然呈现,就能达到内心的静定。王阳明则从本体论的高度指出:“定者,心之本体……动静者,所遇之时也。心之本体故无分于动静也。理无动者也,动即为欲,循理则虽酬酢万变而未尝为动也。”(《答陆原静》之二,《阳明全书》卷二)对此,陈来先生认为,阳明说定者心之本体,包含了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表示动静是意识现象层次的规定,并不适用于本体,心之本体是无所谓动静的;另一方面表示那种平静而无烦扰的境界正是心的本然状态。(参见陈来,1991年a,第79页)这一分析十分精当。一旦我们的境界达到了心之本体的定境,一个人尽管思虑百端、酬酢万变,他的内心依然平静而无任何纷扰。这也是明道努力寻求的境界。在阳明后学中,聂双江、罗念庵也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前进。(参见林月惠,第515-537页)从象山、慈湖到阳明及其后学对定心的重视,可以看出,道学也好,心学也罢,通过内在心性修养,以天理来宰制内心,求得内心的平静,仍然是它们共同探讨的主题,道学心学的分歧只是思维路径的不同罢了。在这里,明道的《定性书》以一种隐性的形式在推动道学和心学的对话,心学对“定心”问题的兴趣也为“定性”话语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
四、结语:几点思考
明道的《定性书》是宋明理学的经典文本,它提出的“定性”话语在宋明思想史上影响深远。“定性”话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演化版本,并提出了许多远远超出本文意义的思想命题,这一文化现象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1.“定性”话语从明道、朱子到西山的发展历程,是一个不断道学化、逐步摆脱佛道影响的纯化过程。
早期理学家多出入佛老,明道也不例外。朱子称:“明道曾看释老书。”(《朱子语类》卷九三)在《定性书》中,明道主张“内外两忘”的定性方法,继承了孟子“不动心”的思想,吸取了道家和佛教的心理修养经验。(参见陈来,1991年b,第85页)仔细分析就可发现,“定性”话语中的“定”与佛之“禅定”之间,“天地无心”、“圣人无情”与道家的“无情以顺有”、禅宗的“无所往而生其心”之间,定性对外诱的排除与道家反对“心为物役”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怪不得叶采称:“愚谓横渠欲去外物之累,便已近于释氏。故程子推其病源,自然与释氏相似。然其自私类于释,而用智则又类于老。要之,二氏用意,皆欲不累于外物而已。”(叶采:《近思录集解》卷二)到了朱子那里,明道的工夫论转化为强调性定的效果论,强调“仁立义行”,重视“性之本体”,豁显出儒家的价值立场。西山更不用说,他反复强调“以道养心”、“以理养心”、“理定于中”、“理即事,事即理”,始终保持天理的主宰以及天理人欲对抗的道学主题。
除此之外,朱子和西山还自觉地对佛老之学展开批判。朱子道学与佛老的对立集中体现在儒家伦理纲常和礼法制度上,故朱子称:“老庄之徒,灭绝礼法。”(《朱子语类》,卷四十)“佛老之学,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废三纲五常,这一事已是极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说。”(《朱子语类》卷一二六)朱子还把矛头指向佛教的理论基石——空论,认为,“佛以空为见,其见已错,所以都错。”(同上)西山也批判了佛老(异端)脱离事物空言道理的空疏无用:“异端言理不及事,其蔽为无用”(《讲筵卷子十一月八日》,《西山文集》卷十八);“其(按:指老庄)以事物为粗迹,以空虚为妙用”(《大学衍义》卷十三)。西山还著有《吾道异端之辨》(《西山读书记》卷三五、卷三六),集中驳斥了佛老杨墨之学的虚妄,极力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
2.“定性”话语的形成、发展与转折,是话语链不断展开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哲理化、本体化、内容不断丰富的过程。
从主题上看,话语链是一个整体性的话语流程,它由一系列的话语片断构成。一般来说,思想的发展演进正是由于一代又一代思想家通过对某一话语链的不断诠释、不断丰富和深化其话语片断来完成的。从明道的《定性书》到朱子的《定性说》再到西山的“定性论”,“定性”话语经历了一个由工夫论到效果论再到本体论的不断深化发展过程,显示出宋代“定性说”的内在发展理路。“定性”话语也由原来的性与情、性与心、动与静、定的功夫等话语片断,逐渐扩展为仁、义、理、中、事等话语,形成一个独特的整体性的话语流程。
朱子和西山的创造性的诠释,则体现了诠释的主体性、时代性、创造性和独立精神,体现了话语研究与现实生活的相关性,为后世思想的伸展提供了新的基点,预设了更为广阔的平台。当然,话语的诠释也与诠释主体自身的价值立场和人生体验密切相关。以此来看朱子对胡安国改削《定性书》的怒发冲冠和反复论辩,其中最可确定的无非就是朱子服膺二程并努力卫道的道统情结。在面对弟子怀疑明道“自私用智之语恐即是佛氏之自私”时,朱子的回答尽管承认了二者的共同点,但也极力划分儒佛的界线:“或问自私用智之语恐即是佛氏之自私。朱子曰:常人之私意与佛氏之自私,皆一私也。但明道说得阔,非专指佛之自私也。”(叶采:《近思录集解》卷二,又见《朱子语类》卷九五,叶采引用时有删节)此外,朱子对仁义和性之本体的重视也是对儒家价值立场的捍卫。
理解既是个体的行为,又是时代的行为。西山对道学的最高本体和现实原则——“天理”的极度提倡,即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基本特征。西山所处的时代,朱子道学被禁为伪学,朱子其学不传,其道不明,当时社会上“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竟,不尊名节而尊爵位,不乐公正而乐软美,不敬君子而敬庸人。既安习以成风,谓苟得至计。良由前辈长老零落殆尽,今之负物望、协公论者不聚于朝廷。后生晚进,议论无所据依,学术无所宗主,正论益衰,士风不竟。”(《刘阁学墓志铭》,《西山文集》卷四三)在这种情况下,西山以“斯文自任”,通过大量的著述和讲学,力倡圣学,弘扬“道统”,发扬道学,使道学重新确立了其正统的地位。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西山始终高擎“天理”的旗帜和力排二氏(佛、老)的苦心孤诣。
最后,当我们谋求某一问题的未来发展时,还必须注意当前话语链中主要话语的改变及与其他话语链之间的相互关系。话语主题的转向也标志着社会思潮的转变。我们看到,当“定性”话语中的主题——“性”被置换为“心”时,“定性”话语的主题发生了根本变化,“定性”学说也完成了向心学主题的转换,意味着道学思潮开始向心学思潮的转变。
3.“定性”话语的展开立足于日常生活世界,强调认知与行动的一致性,恰好与话语分析所坚持的基本原则相吻合,也有力地证明了话语分析方法在道学思想研究乃至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优先地位。
针对张载因日常生活受到外物的干扰无法获得内心宁静而发出的疑问,明道的精彩解答成就了一个经典学说——“定性说”。明道的“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绝非纯粹理论指导;它直接指向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如何展开行动,或者说,认知的落实才是最重要最关键的环节。朱子强调“存养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要有“存养”,要“功至”而后才有“得”;“得”的前提就是行动,它不指示纯粹的认知。西山讲“体”不离“用”,讲“以道养心”、“以理养心”,对“用”和“养”的重视也是如此。简言之,道来自“伦常日用之中”,知“道”的目的是为了践“道”、行“道”,这正是儒家哲学的一贯立场。
与儒家哲学立场相类似,话语分析非常重视话语与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关联。“话语分析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对一个话语链或一团相互交织的话语链进行历史性的分析或与现实相联系来分析;同时还应做到对话语链在未来的进一步发展趋势做一些谨慎的说明。”(耶格尔,第145页)话语分析的基本问题是话语与语境的关系问题,我们说话的内容与方式都与我们所处的日常生活世界密切相关。话语依赖于这个世界,话语意义与它的语境息息相关,同一话语在不同语境中意义甚至完全不同。同儒家“知行合一”的传统相仿,话语分析不仅仅是理论分析,它也指向社会实践,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行动(在指向社会行动方面,批判性话语分析尤为突出)。在与语境和世界的关联中,约翰斯通(B.Johnstone)认为,话语分析不但要重视说出来的话,更要重视没说出来的话和说不出来的话。话语是前景,沉默是背景。(Johnstone,p.152)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在“定性说”整套话语的背后究竟隐含着什么,那么,透过明道、朱子和西山的文本,我们可以读出道学家们对释老的排拒,读出对儒家价值的渴求,读出对心灵的安顿与提升,这也正是中国哲学一贯的隐喻言说和“微言大义”的传统。
尽管话语分析已趋向于避开对抽象或理想化结构的研究,笔者却认为,话语分析相对于曾在当代中国哲学界广泛流行的“范畴体系”研究仍有它的优先性。陈来先生指出,范畴体系研究“可以在范畴系统的一般特征方面显现出中国哲学与欧洲哲学的不同,但范畴的研究如果离开了具体问题的讨论,不是从具体的哲学讨论中理解范畴概念的意义,就只能停留在一般的、笼统的说法上,而无法真正促进我们对中国哲学基本概念和具体讨论的理解。”(陈来,2003年,第25页)这里的“具体问题”即“具体语境”;对哲学话语的理解离不开它的具体语境,只有把哲学概念和范畴放进特定的时代和生活境遇中进行分析,诠释出其中沉默的“微言”和“大义”,我们才能达到对中国哲学基本概念和内在精神的真正把握。在这一点上,话语分析方法无疑具有更大的普适性和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