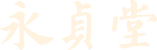儒家经学中的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西汉中期儒家思想独尊,其典籍上升为“经”,而“经”有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的文本和以后发现的用籀文书写的文本。前者称之为今文经,后者为古文经。儒生讲经所据的文本不同,因而有今古文学之别。
今文学派 西汉初年所传儒家经典都是今文经,因为经过秦代的“焚坑”之后,儒家经典只能靠儒生们口耳相传,然后用汉代隶书写成文本。由于传经的师承家系不同,所传的虽同属一经,也有各“家”的区别。汉代所立“五经博士”有14家之多。即《周易》有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4家;《书》有欧阳生、大小夏侯3家;《诗》有齐、鲁、韩3家;《礼》有戴德、戴圣两家;《春秋》当时立《公羊春秋经传》有颜、严两家。立于学官的经学博士亦即朝廷认定的经学流派,通一家经学,即可入仕为官,成为儒生走进统治阶层的“正途”。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大一统的政治结构趋于稳定的时代,形成于这样政治背景下的儒家今文经学以服务于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大一统帝国为其旨归,因而在儒家经典中以“微言大义”为政治提供理论根据的《公羊春秋》最受今文经学家的青睐。最有影响的汉代儒者董仲舒和何休都是以治《公羊春秋传》闻名的。今文经学由于其屈从政治需要而流于附会,进而与谶纬迷信结合而流于妄诞,加之拘于师承家法而愈益繁琐,因而在古文经兴起后逐渐趋于衰落式微。而其因时而变通对儒经的解释、随时代需要而賦于旧说以新义的学风则是对恪守训诂轻视义理的“古文经学”的补充,对后世儒家经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古文学派 西汉立于学官的经学开始都是今文经学。而据说是从孔子宅壁中发现的儒经则是用“古文”(籀文、篆文)书写的文本。其实是些“不知时变”的儒生在民间习用的与用隶书写成“今文”有别的儒经。今古文之别不仅是书写文字上的区别,更重要的是“官学”与“私学”之别。
西汉末,外戚王莽篡汉改国号为“新”,但却刻意复古从旧,仿效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以古文经的《周礼》为据改革汉代的典章制度,因而大力提倡古文经,并凭借政治权力将古文《周礼》《春秋左氏传》《毛诗》《古文尚书》立为学官。古文经为当世所罕见,与常见的今文经学发生激烈冲突。王莽谋士刘歆作《移太常博士书》就是站在古文立场上攻击今文。今文讲谶纬,而王莽好符瑞,因而虽提倡古文,却不废今文。
今古文之争 东汉今古文并行。今文与谶纬结合,获朝廷支持。古文经学一旦立于学官,习古文的儒生亦可入仕做官。加上古文经学的内容丰富,民间习古文经学的儒生为数不少,当时名儒授徒,从学者动辄以百千计。最著名的是贾逵、马融、郑玄。当时的今文经学大师何休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均佚)反对以贾逵为代表的古文学派。而郑玄也作《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均佚)以示反驳。由于郑玄博通今、古文,在注经中虽以古文为主,却综合两家之长,把今文经学的一些方法融入古文,从而使今古文之争逐渐趋于平息。随着魏晋玄学的兴起,汉代经学日益式微。汉灵帝熹平四年(175)立蔡邕所书《六经》于太学标志着今古文之争告一段落。
两种学风 今古文学既是两个流派,也是两种学风。古文经学遵循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精神,讲求字义名物训诂,也遵循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精神,不去附会谶纬,但却忽视义理蕴含的阐发,不能通时达变,适应当时朝廷的政治要求。在整个汉代,除西汉末和新莽时期外,古文经学基本上处于“民间”状态。而今文经学则通时达变,投人主之所好,附会经义,杂以谶纬,以致流入浮夸妄诞,曲解经义,但却富于“创新”,敢于合乎时宜地阐发新义,不断对经义做出再解释。如《春秋公羊传》开始讲:“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里本就历法而言,而董仲舒讲:“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同“义”)也。”(《汉书·董仲舒传》)这就完全变成了政治概念。
东汉士人做官主要通过“征辟”之途,不必习经,而习经者要恪守“师法”,愈益繁琐,形成“幼童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汉书·艺文志》)的局面,在失去政权的强力推崇支持后,今文经学走向衰落是不可避免的。
影响 汉代的今古文学之争对后世的经学发展产生了持久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取代经学,在内容上援道入儒,把玄远哲理注入儒学。王弼注《易》,尽扫汉代孟喜、京房之象数。何晏注《论语》、杜预注《左传》、范宁注《穀梁》,均辞意简略,括其要旨,一反两汉繁琐之风。南朝经学本“江左玄风”之精神,重在义理,兼顾训诂,融会今古文之长,因而使汉代经师注经之作除少数留存(《毛诗》、郑注《三礼》、杜注《左传》、范注《榖梁》、何注《公羊》)外,大都佚亡。其中只有何休所注《公羊》为今文外,其余全为古文,这个局面延续到隋唐统一之后,成为公认的正统。由唐太宗、高宗“钦定”,由孔颖达所作的《五经正义》更进一步肯定了这个局面。《五经正义》持“疏不破注”的原则,保留了南朝经学之风,也统一了南北经学。此后经学的发展进人新阶段,今古文之争演变为学风上重训诂与重义理的不同侧重之争,以及在方法态度上的“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之争。
儒学发展到宋代,在思想内容、理论结构和学风旨趣上都发生了迥异于汉代经学的重大变化。宋学与汉学的不同的趋向在深层次上与历史上的今古文之争有着某种历史渊源。宋学重义理,敢于疑古,敢于创新。如欧阳修作《易童子问》,怀疑十翼非孔子所作;张载有“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的理论勇气;朱熹敢以己意作《补〈大学〉格物致知传:h陆九渊有吾心即是宇宙之论。这些都是汲取佛、老哲理精义后理论思维水平的飞跃,是摒除了今文经学的谶纬迷信等非理性主义糟粕,而又发扬了其因时宜而赋予儒经以新义的精神,加之破除了汉代经学拘于“师法”的僵化保守,使哲理性的气、道、理、心等范畴成了最高的理论依据,是“圣人”所传的真精神。把经学哲理化是宋学的一大贡献。宋学中的程、朱理学一派还比较重儒经原义,注经时还讲求一下训诂,而陆九渊(以及明代的王守仁)的心学一派则认为“学苟知本,则《六经》皆我注脚”(《象山全集》卷三十四)。理学一派虽强调“理”的外在客观,但却也“师心自用”。如朱熹既怀疑古文《尚书》之真,又认为《皋陶谟》中“人心惟危……”等四句为圣人“心传”。在一定意义上说,宋学的学风是今文经学重义理重开拓学风在新时代的升华再现。而清代出现的乾嘉朴学是汉学中古文经学重名物训诂传统的复归(故乾嘉朴学亦称新汉学)。乾嘉朴学在学风上虽弃宋复汉,重考据不重义理,但却继承了宋学的勇于疑古之风。清中叶后,在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促使下,儒生中一些有识之士又到今文经学中寻求变革现状的理论武器。孔广森著《春秋公羊通义》首倡今文经学,刘逢禄、宋翔凤继之,刘作《春秋公羊传何氏注释例》,发挥张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存三统(夏、商、周)思想。此后,龚自珍、魏源亦以今文经学立场主张通经致用。而清末的康有为作《大同书》时亦以公羊三世说为依据,又作《新学伪经考》,把古文经学斥为新莽时刘歆之伪造,又作《孔子改制考》,宣传“托古改制”。如果说康有为是今文经学的最后“殿军”,那么曾是近代民主革命宣传家的章炳鱗则成为古文经学的最后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