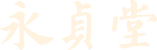宗教伦理思想是丘处机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翻阅丘氏的著述,诸如道德、仁义、修阴德等术语几乎屡见不鲜,倘若再认真加以研读,不能不感受到在这些术语中蕴含着一份浓浓的伦理情怀。丘氏所以有这份浓浓的伦理情怀,盖缘自他在修道践行的活动中对天道与人道、社会与人生,以及善与恶、福与祸、苦与乐等问题多有了悟和阐发,从而成就了他独具风格的伦理思想。概而言之,他的宗教伦理主要统摄功行双修、行善进道、忠孝仁义等三个方面内容。
一、功行双修论
山东全真家作为出家住庵修道的道派,它一开始就遇到了道与俗、出世与入世、做人与成仙等矛盾的挑战。因此,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将既关乎到山东全真教的自身生存发展,又关乎到它选择怎样的行为方式才能同世俗生活和世俗伦理保持协调一致的问题。祖师王重阳为了化解与协调这些矛盾,他同修炼方式上的性命双修相匹配,在《玉花社疏》中提出了“真功”与“真行”相结合的主张。他所说的“真功”系指澄心定意、致虚守静等心性的修炼,“真行”则指积德行善、“济贫拔苦”等道德践履活动。简言之,真功就是清静修炼,真行就是济世救人,只有功行双修、把两者统一起来,方可获致成仙的可能性。祖师的真功真行对山东全真七子影响很大,其中丘处机对这种思想广大发扬最为显著。
丘处机首先对功行做了新的解读。《长春丘真人寄西州道友书》记载了他与弟子友人的许多问答对话,其中“又问内外日用”,丘曰:
“舍己从人,克己复礼,乃外日用。饶人忍辱,绝尽心虑,物物心休,乃内日用。”次日,又问内外日用,丘曰:“先人后己,以己方人,乃外日用。清静做修行,乃内日用。”又曰:“常令一心澄湛,十二时中,时时觉悟,性上不昧,心定气和,乃真内日用。修仁蕴德,苦己利他,乃真外日用。”[①]
不难看出,所谓“内日用”系指以真清真静修治心性的工夫,也就是重阳祖师所标榜的“真功”,其属于修仙成仙和出世的范畴。而“外日用”则指以己虑人、先人后己、苦己利他,以及克己复礼、主动服从社会规范制约的道德行为,其属于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的伦理道德范畴。这里,丘氏把功行的修治视作“日用”关系,就意味着神仙生活和道德生活离人不远,它们就在你的身边,作为修道者完全有可能将两者统一起来。而他把功行的修治视作“内外”关系,此则意味着功行双修对于修道者是缺一不可的,故而所谓功行双修,亦即是内外双修。处机对功行双修的这种解读,不仅使重阳祖师的真功真行变得通俗易懂,而且也主动消解了全真道士所遇到的道与俗、出世与入世、成仙与做人的紧张与冲突,这无疑是对重阳真功真行思想的拓展。
其次,丘处机把积行累功作为升道成仙的前提条件。《长春丘真人寄西州道友书》说:
大抵修真慕道,须凭积行累功。若不苦志虔心,难以超凡入圣。或于教门用力,大起尘劳;或于心地下功,全抛世事。”[②]
所谓“或于教门用力,大起尘劳”,即批评那些身在道门却劳作于尘世而不专心修行的人;所谓“或于心地下功,全抛世事”,则赞扬那些专心致志做清静“内日用”工夫而不染世俗的真正修道者。由此,丘处机认为无论做“内日用”的功业抑或做“外日用”的修行,都不是一朝一日就能获致的,而是经历了累世积淀的过程。
悟道之人,如农家之积粟,自一合至万石。又如世人之积财,自一文至万贯。如此惜气不损,则积气自神矣。”[③]
这种“积行累功”之所以成为修道者的根本需求,是由于修道的主体始终“克己存心于道,皆为致福之基”,“坐卧住行,心存于道,虽然心地未开,时刻之间,皆有阴德积累。”但是丘处机也承认,由于“道包天地,其大难量,小善小功,卒难见效”,故欲达致“刹那悟道”更“须凭长劫炼磨”,“顿悟一心,必假圆修万行”[④]。根据丘氏对内、外日用的诠解,累功业体现了修道者的神学归属,积行德则体现了修道者应尽的社会责任。而丘氏认为累功业须经“长劫磨炼”,积德行须“假圆修万行”,这就意味着个体的宗教归属与其所履行的社会责任既是统一的,又是长期的,从而协调了以前道教所遇到的那种道与俗、宗教与道德之间的尴尬场面。
复次,丘机用轮回报应说论证积行累功的必要性。他摒弃了传统道教承负说,借鉴佛教的轮回报应思想,将修道成仙视为积累善果的过程。但丘处机认为,这个善果的积累不包括祖辈的善果,亦即祖辈功行无法承负给子孙,唯独修道者本人的功行才能随其轮回报应流转到现世,故修道者自己的功行是决定其能否入道成仙的关键。《寄西州道友书》说:
今世之悟道,宿世之有功也。而不知宿世之因,只见年深苦志不见成功,以为尘劳虚诞,即生退怠,甚可惜也。
所以修治功行,“惟患人心退怠,圣贤不能度脱。若不退脱,今世来世,累世提契,直至了达耳。”[⑤]这些话一方面把修道者的功行视作上世、现世等历世积累的结果,强调修真者具备累世功德才能成为神仙;另一方面又劝戒那些“不知宿世之因”的今世修道者,不要因为自己在现世未摘得正果而意志怠惰和消极衰退下来。因此,丘处机告诫道徒要认真对待今世的功行积累,指出今世未能悟道的根本原因在于“功之未足,则道之不全”,但这不等于你没有“阴功积累”,只要你肯“心存于道”,“虽未得道,其善根深重,今世后世,圣贤提挈,方之无宿根者,不亦远哉?”丘氏还以自己为例说:
我无宿骨,虽遇明师,万苦千辛,于今未了。丹阳、长真皆是宿缘,则十年五载之间,天外飞腾自在。我虽未了,所受艰难亦与常人异耳。[⑥]
丘处机作为七真中的出类拔萃者,他说自己没有“宿骨”,这当然属于谦辞,但他说上述一番话的目的旨在鼓励道徒努力做全功行积累的修治,这既体现了道教所一贯具有的“我命在我不在天”的主体能动精神,又从理论上化解了道徒对修道长短、得道迟速问题的困惑,同时还使修仙与伦理佐世得到了和谐一致,因而对促进全真道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二、行善进道论
“善”作为对伦理道德正向价值的肯定,中国古代先民很早就使用这个范畴。仅就儒、道两家来说,《尚书·汤诰》即有“福善祸淫”说,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九章则说:“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后来,道教首经《太平经》曾广泛使用“善”这个范畴,如说:“人君为善于内,风雨及时于外,故瑞应反从人胸中来。”[⑦]山东全真家在架构其伦理道德思想时也运用了“善”的范畴,其中丘处机在论述自己的功行双修、内外日用的同时,又进一步将伦理之善与进道成仙整合在一起。
对此,《玄风庆会录》云:
行善进道,则升天为之仙;作恶背道,则入地为之鬼。
夫道产众生,如金为众器,销其像,则返成乎金。人行乎善,则返乎道。
但能积善行道,胡患不能为仙乎?
既获难得之身,宜趣修真之路,作善修福,渐臻妙道。[⑧]
丘处机所论说的“道”,既是指宇宙本体,又是指价值本体。当“道”转化为仙道时,它就成了修道者所渴慕的神仙信仰、境界或偶像。丘氏认为修道者只有行善、积善、作善才能进道、行道、达于妙道,以及最终成为神仙,这就意味着“善”的价值乃是道和神仙的本性本相,作为修道者的善言善行虽然还不能直接说成是道和神仙之善性善相的启示,却透露出道徒惟有修善向善才能步入神仙不死的境界。这样一来,“善”在丘处机这里便取得了宗教伦理的意义,并标明山东全真道教创建伊始即是一个向“善”的道教支派。
难能可贵的是,丘处机所说的“善”不啻具有宗教伦理的意义,而且还具有直面社会、人生的现世价值。丘氏在西行时,曾劝说成吉思汗“行善修福”,即谓:
帝王悉天人谪降人间,若行善修福,则升天之时,位逾前职。不行善修福,则反是。天人有功微行薄者,再令下世,修福济民,方得高位。
为了达到劝说大汗的目的,丘氏还托古以张其说,谓:
昔轩辕氏,天命降世,一世为民,再世为臣,三世为君,济世安民,累功积德,数尽升天,而位尊于昔。
由此,丘处机便向成吉思汗直陈怎样行善修善,即:
陛下修行之法无他,当外修阴德,内固精神耳。恤民保众,使天下怀安,则为外行;省欲保神,为乎内行[⑨]。
不难看出,丘处机向成吉思汗所要求的“行善”系以“济民”、“安民”、“恤民”为内容。这种带有儒家色彩的民本思想虽然是借轮回报应的神学形式加以阐发的,但此对于当时只知道尊天敬天而不懂得“民本”为何意的落后的蒙古上层贵族集团来说,也许是一种最容易使他们接受、最不容易激化他们的逆反心理的宗教形式。而丘处机借轮回报应劝蒙古大汗“行善”,这不仅弘扬了中原文化关于“善”的道德价值,而且也表现了山东全真道士所怀具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人文精神。
三、忠孝仁义观念
任继愈先生说:“金元时期的全真教把出家修仙与世俗的忠孝仁义相为表理,把道教社会化,实际上是儒家的一个支派。”[⑩]任先生把全真教判为儒家一个支派不一定得到学界的认同,但全真教吸纳了儒家伦理思想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祖师重阳在《授丹阳二十四诀》中所说的“若修行之人,仁者不弃,义者不污,礼者不自高,智者不争,信者不妄言”[11],就全面接受了儒家的“五常之道”;而他在《金关玉锁诀》中说的“忠君王,孝敬父母师资,此是修行之法”[12],则标明他把忠孝伦理纳入了道戒的范畴。在祖师的指点下,全真七子对儒家伦理观念均有吸纳,特别是谭处端说的“忠孝仁慈胜出家”[13],更表现了全真教浓重的儒家伦理情结。
在“忠孝”观念上,丘处机虽然直接讲“忠”字不多,但他在西行谨见成吉思汗的过程中却以实际行动向大汗表“忠心”。像他向大汗讲以不嗜杀人作为“一天下”之方、以敬天爱民作为“为治之方”,以及向大汗讲“以清心寡欲”作为卫生之经等,都属于对前元蒙古贵族首领的尽忠行为。至于讲“孝”,丘处机除了向大汗弘扬“人罪莫大于不孝,不孝则不顺乎天”[14]的儒家“孝”文化外,他本人亦非常重视“孝”文化的习读,将《孝经》作为日诵之典。正是由于孝文化的习染熏陶,丘氏虽然出家修道传道在外,但他却对自己父母深怀眷恋、崇敬之心,特别是当他得知栖霞父老乡亲为其父母合葬的消息后,其怀念父母和感激乡亲的心潮起伏澎湃,乃秉笔创作《满庭芳》以答谢乡中善士为葬先考妣,曰:
余因求道,西留关中十五余年,闻乡中善士为葬先考妣,不胜感激,遂成小词寄谢云。
幼稚抛家,孤贫乐道,纵心物外飘蓬。故山坟垅,时节罢修。崇幸谢乡豪并力,穿新圹、起塔重重。遗骸并,同区改葬,迁入大茔中。人从。皆言盛德,悉报微躬。耳闻言,心下感念无穷。自恨无由报德,弥加志、笃进玄功。深回向,虔心道友,各各少灾凶。[15]
在儒家文化中,忠与孝是密切相联的两个概念,忠强调为国家、为社会、为君王,孝则强调敬养父母。古代社会虽有忠、孝不能两全的说法,但忠臣爱国之士则必定是孝悌之人,丘处机在忠孝问题上亦可作如是观。他正因为做到了忠孝两全,所以清末龙门派道士陈铭珪(即罗浮酥醪洞圭陈教友)评价丘处机说:
长春学于重阳,观所作诗词,虽一死生,遗万物,而忠孝之性,一感触之,油然自生,其服习于《孝经》者深矣。
可见,丘处机一生将成仙与忠孝的结合,已达到了圆融完美的境地。
孔子在《论语·学而》篇曾把“孝悌”视作“仁之本”。此即意味着大凡讲孝悌的人必然也讲仁义。丘处机虽然直接提到“仁义”二字较少,但他把“修仁蕴德,苦己利人”作为“真外日用”,已经内含着对儒家仁义之德的深刻省悟。由于丘处机是立足于修道成仙和民生日用的实践活动来运用仁义观念的,所以他很少教条式的照搬儒家的东西,而是根据理论建构的需要灵活地加以创造转换。例如,当成吉思汗以“至礼”接待丘氏时,丘处机则“告之以清静无为之方,上帝好生,一代仁厚之风,皆从此二句起。”[16]意即大汗只要肯以清静无为治国,关爱百姓的生命,不滥杀无辜,就能形成仁厚的社会风气。这种儒道整合的释“仁”方式,无疑是丘处机的新创,并内含着深刻的社会关怀思想。又如,当有人向丘处机问“如何是仁体”时,丘氏答曰:
仁者,生也。一点生机,鸟啼花放,山色波光,俱为造化,……一念不生为仁体,万行皆圆为仁用[17]。
此之“生”具有生命、生机、生生不息之义。丘氏以“生”释“仁”,可谓最大限度的发挥了《易》之“天地之大德曰生”之义,并表现了他对个体生命的深切关怀。而丘氏把摈除一切杂念私欲视作“仁”之体,把道德万行视为“仁学”的发用,这完全是从体、用关系来解读仁与道德万行的关联性。这样一来,丘处机对“仁”的解读就超出了道德范畴或道德行为的视阈,而是赋予“仁”以本体、境界或世界观的意义。因此,尽管丘处机在自己的著述中没有花费很多笔墨谈仁讲义,但由于他是以哲学慧识解读仁义的,所以较之其他全真六子多有精湛之处。
更值得关注的是,丘处机在解读仁义时总是把社会关怀、个体生命关怀与现实关怀密切结合在一起。当百姓大众岁遭饥疫灾害时,他悲天悯人,高呼“天苍苍兮临下土,胡为不救万灵苦”[18];当民不聊生而无法活命时,他要求学道之人济物利人,将“饮食、居处、珍玩、货财亦当依分”[19];当世俗之人贪恋酒色财气而一味追逐物欲时,他以道、仙的“至乐”观告诫世人,此是“以妄为真,以苦为乐,不亦悲乎?”[20]丘处机所阐述的这些普救众生、济物利人,以及提倡节俭、反对奢侈腐化的道德主张,可视作其以“生”为核心价值的“仁体”在现实人伦万行中的发用,此不仅进一步丰富了他的伦理哲学的内容,而且对发展我们今天的道德伦理文明也留下了值得开掘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