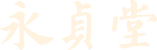陈洪绶以书画知名,鲜为人知的是,绘事之外,他亦寄情声歌,通晓曲律。晚明在中国戏曲史上的成就堪与元代媲美,文人传奇盛于此时,作家蜂起,佳作如林。陈洪绶虽然本人没有直接参与戏曲创作,但他与晚明曲家之间有着密切的交往与深厚的情谊,这些交往与情谊也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在他的诗画创作之中。
陈洪绶生活的晚明,越中一带聚集了众多优秀的曲家,其中与他最称莫逆的当数孟称舜、祁豸佳家族与张岱兄弟。
陈洪绶与孟称舜
孟称舜被认为是戏曲“临川”派继汤显祖之后最重要的作家,倪元璐称他为“我朝填辞第一手”,他编撰的《古今名剧合选》,是公认元明杂剧的一部重要选集,其中收录杂剧五十六种,包括他自己的《眼儿媚》、《桃源三访》、《花前一笑》与《残唐再创》四种,全书由孟氏详加评点,是古典曲论的重要典籍之一。其中孟氏剧作全由陈洪绶评点,加上亦由陈氏点评的《节义鸳鸯冢娇红记》,陈洪绶堪称目前所知点评孟氏剧作最多、用力最勤的批评家。陈氏的评语,既有宏观的艺术特色、价值取向的剖析,更有微观的铸词冶句、叶韵入律、传情写态、情节设置等的点评,如其评《桃源三访》:“《桃源》诸剧旧有刻本,盛传于世。评者皆谓当与实甫、汉卿并驾。此本出子塞手自改,较视前本更为精当。与强改王维旧画图者自不同也”;评《娇红记》:“若铸辞冶句,超凡入圣,而韵叶宫商,语含金石。较汤若士欲拗折天下人嗓子者,又进一格”、“此曲之妙,彻首彻尾一缕空描而幽酸秀艳,使读者无不移情”;评《泣赋眼儿媚》:“蕴藉旖旎,绰有余致,而凄清悲怨处,尤足逗人幽泪”等等,不一而足。《节义鸳鸯冢娇红记》是孟称舜最著名的传奇,曲苑有“临川让粹,宛陵让才,松陵让律”的美誉。
与祁彪佳、马权奇等曲评家一样,陈洪绶对《娇红记》极为赞赏,不但为其作了四幅精美绝伦的卷首插图,更详加评点,亲作长序。在序言中,陈洪绶表达了对孟称舜——也可以说是对当时曲作家们——的深刻理解:孟称舜才华过人而以道气自持,每每被“乡里小儿”视为迂生腐儒,实则情深一往,他所追求的至情至性,“问诸当世之男子而不得,则以问之妇人女子;问诸当世之妇人女子而不得,则以问之天荒地老古今上下之人”。或有“老先生”见到孟氏所作的戏曲,呵斥其为“不正之书”,陈洪绶为他辩驳:“今有人焉聚徒讲学,庄言正论,禁民为非,人无不笑且诋也。伶人献俳,喜欢悲啼,使人之性情顿易,善者无不劝,而不善者无不怒。是百道学先生之训世,不若一伶人之力也。”这又是对地位低下的伶人们的肯定与认同。陈洪绶一生醇酒妇人,放浪形骸,但其诗文却多有沉郁的家国之痛,至情至性,一往情深,他与孟称舜性情相近,所以相知最深。
陈洪绶与祁氏叔侄
绍兴祁氏家族历代为官,书香门第,其中祁豸佳、彪佳、骏佳诸兄弟;奕远、奕喜诸子侄辈皆为一时名士。祁豸佳与祁奕远分别蓄有家班,他们精通曲律,常自创新剧或自度曲子,教授伶人,阿宝、鲜云等名优皆出于门下。祁彪佳更是晚明越中地区最重要的曲家与评论家之一,他的《祁忠敏公日记》记载了晚明绍兴一带大量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戏曲活动,其所著的《远山堂曲品》与《远山堂剧品》是明代最浩繁的戏曲批评专著。陈洪绶与祁氏家族两代都有深厚的交谊,他有两首赠予祁豸佳的五言律诗,中有“同是沉沦客”之句;陈、祁二人都有戏曲、书画之好,早年又皆屡困场屋,经历志趣十分投合。陈氏晚年困顿,除以卖画自给外,经常需要朋友的接济,有时连作画的纸也需要朋友赠予,友朋中以祁骏佳叔侄最多施以援手。陈氏文集《宝纶堂集》中,写给祁骏佳的诗有五首,与祁奕远的唱和多达几十首,如《郑履公、祁奕远、刘道迁与老莲葺屋若耶溪上,期金道隐来避乱,不至》、《卜居薄坞,去祖茔三四里许。感祁季超(骏佳)、奕远叔侄赠资》、《寄谢祁季超赠移家之资,复致书吴期生,为余卖画地,时余留山庄两月余》、《奕远赠予移家之资,却赠,即书扇上》……“移家仗亲友,守墓近松(木秋)。不幸中之幸,两贤何处求”、“连年衣食子,兵乱尚分金。劫掠无余际,相怜复尔深”、“赠金忘感谢,十载受轻财”,这些诗作充满了祁骏佳、奕远叔侄对陈洪绶的深情厚意以及陈氏对他们帮助周济的感激之情,这亦从另一侧面反映出陈氏晚年生活的窘境。
陈洪绶与张岱
除了家乡绍兴,杭州是陈洪绶居留时间较长的地方,在这里,与他交往最密切的是晚明著名的小品文作家、也是最重要的曲评家张岱。陈洪绶最经典的作品之一《水浒叶子》就是在张岱的敦促下历时四月完成的。张岱出身名门,世代簪缨,家中广造园亭,富有藏书,从祖父辈就开始蓄养家班,到张岱时已有可餐班、武陵班、梯仙班、吴郡班、苏小小班、茂苑班等,名伶层出不穷。张岱自己也是个精通曲律的大行家,经常参与各种演剧活动,优伶们对其异常敬畏,称在他面前演出为“过剑门”,意即须万分小心谨慎,以免出乖露丑。
张岱作有一出杂剧《乔坐衙》,剧作失传,不过陈洪绶为其写的题辞则流传下来。“乔坐衙”是当时的一句俗语,意即装模作样,装腔作势,陈氏题辞中有“宗子其人得闲而为声歌,得闲而为讥刺当局之语,新辞逸响、和媚心肠者,众人方连手而赞之美之,则为天下忧也”之语,可见张氏所作的是一出讽刺剧,而陈洪绶在赞叹张氏“才大气刚,志远学博”之余,也为其不得施展抱负而寄情声歌感到不平。与同祁氏家族的交游一样,陈洪绶不仅与张岱是知交,与张氏兄弟都堪称莫逆。张岱弟兄的确切情况并不十分清楚,根据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张氏有四弟,分别字卿子、介子、平子、登子,而张氏文集中有《赠名子弟》诗,且《陶庵梦忆》中讲到家班时有“名子茂苑班”,则还有一弟名子。陈洪绶崇祯庚午年(1630)为张平子迁入新居画人物为赠,又曾为其诗集《品山拈》写序;上海博物馆藏有陈洪绶作于丁亥年(1647)的行书册页三开,内容是酬谢张名子赠米。张氏兄弟中,除了张岱,陈洪绶似乎与张登子最为亲近,他的诗集中写给登子的诗有八首,其中一首写道:“几年不见张公子,每忆玄都观里人。常梦云间同作客,数回吹笛唤真真”,这是借用了元人杨维桢写给画家张中的诗,与他题在张中《桃花幽鸟图》上的几乎完全一样,只有数字之易,可见张登子也是位倜傥多才的佳公子。
同样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杂画册》四开,描绘四处园亭景致,画无款识,造型画法是典型的陈氏风格,画后的题跋提到了陈洪绶,称此画为“登老”所作,画的就是“登老”的别业。张氏家族园亭之美为越中之胜,陈洪绶写给张登子的诗中亦有“不到张生丘壑久,胸中丘壑竟无多”之句,则此“登老”极有可能就是张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