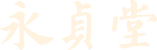一、问题的提出
《论语·子罕》“可与共学”章载: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这三段话涉及四个概念:“共学”“适道”“与立”“与权”,姑称之为三段四言。孔子以“可”与“未可”来表明三段四言的层层推进之关系,构成一套言说系统,反映的是孔子人生哲学的智慧。不过其结语却是“未可与权”,似乎表明“权”在孔子心目中分量很重而未可轻易“与”之。那么,此“权”字究为何意?历来的主流解释以为此“权”乃“权变”或“反经行权”之意,此解是否成立?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一般认为,“未可与权”乃是儒学史上有关“经权”观的最早案例。如所周知,儒家经权观表明在德行实践过程中须注意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既要坚守纲常原则,又要在具体的现实场景中注意原则运用的合宜性。而上引三段四言表述清楚、语意连贯,似乎并无难解之处,以至于朱熹(1130-1200)在解释这段文字时,仅对“可与”两字作了解释:“可与者,言其可与共为此事也。”①
然而,若按“可与”即“可与共为此事”之意来理解,那么前三句所言“共学”“适道”“与立”都不难解释,只是第四句“与权”究应如何理解却不免犯难。因为孔子之意甚明显,即在“未可与权”这一否定性命题的背后,其真正期望的却是“可与权”——“可与共为此权”。若此权盖指权变,那么“可与权”就不得不解释成“可与共为行使权变”。难道“可与共学”章的终极目标却是追寻“可以共同行使权变”之人?如此一来,行权或权变岂非成了最高层次的德行表现了?②因为事实很明显,上引三段四言构成一套系统,故“与权”必然是前三者的推进结果,但是“可以共同行使权变”倘若成立,则势必导致儒家德性伦理学的根本改观,即对于伦理纲常的经的坚守必须退位于“反经合道”的所谓“行权”③,由此则权岂非逆而上之、反而位在经之上了吗?
的确,就字义看,经之本义为“织也”,与“纬”字相对,意指直线,引申义则为常、不变、原则等;权之本义为“秤锤”,引申义则为权衡、通变或权变,与经恰成相对之词。在儒学史上,“权”字的最早案例出自《论语·尧曰》引“尧舜咨命之言”,即“谨权量,审法度”之说,朱熹释:“权,秤锤也;量,斗斛也。”④在儒学史上,有关权的典型叙述莫过于孟子的一段话:
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离娄上》)
这是儒学史上明确地将权与礼(即经)对置而言的首例,而此权字的引申义便是应权通变。故此,许慎(约58-147)《说文解字》以“反常”一词来定义权⑤,是不无道理的。清代文字学家段玉裁(1735-1815)《说文解字注》亦承此说,且分别引《语》《孟》《公羊》之说予以说明,其中便有孔子的“未可与权”说。段玉裁指出:
一曰反常。《论语》曰“可与立,未可与权”;《孟子》曰“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公羊传》曰“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
这是将“未可与权”的权理解成反常或反经,即权变之义。然而,文字学家的这种史料罗列并未告诉我们其义理上的依据,这将导致一种严重的理论后果:孔子“与权”说竟与公羊学“反经”说一般无异。问题显然相当严重。
对孔子“与权”说应如何理解?其“权”字究为何意?历史上的主流解释以此“权”为“权变”是否妥当?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及解答,不仅将有助于我们重新省察孔子乃至儒学经权观的思想意义,而且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孔子人生哲学的旨趣亦有裨益。
二、汉儒以“反经”说“权”
从历史上看,行权问题自孔子提出以后,主要以两条线索展开:一是孟子的“嫂溺援之以手,权也”,一是《公羊传》“权者反于经”。孟子之权主要着眼于个人道德领域,而《公羊》之权则主要着眼于社会政治领域。领域虽不同,然此权字之义所指则同,即均指向“权变”或“应权通变”。只是孟子所言之权,强调在道德两难之际,应舍轻就重、变通原则,做出合乎时宜的道德选择,就此而言,权是德行实践过程中应正视的应变方法,而此道德选择又须以德性原则为根基⑥,因此可以说这是儒家伦理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一点本不难理解。然而,在《公羊》“反经”的主张中,却可看到权变有可能背离纲常伦理而沦为权术或权谋,这就引起后世儒者的警觉。此且从《公羊传》之论权说起。
《公羊传》“桓公十一年九月”载祭仲“行权”事,事情原委且姑置勿论,《公羊传》在解释祭仲选择“出忽而立突”⑦的行为时,大赞其“知权”,进而指出:
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权之所设,舍死亡无所设。行权有道,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为也。⑧
就这段文字的整体看,讲得似很得体,特别是“行权有道”说反映了《公羊》“行权”思想的大义,以为行权不当以“害人”“自生”或“自存”为前提,相反,应做到“自贬损”,这才是“行权有道”,此本未可厚非。然而,招致后儒非议的乃是其背反君臣伦理的“反经”说而非“行权有道”说。因为很显然,祭仲“逐君立庶”⑨之行为是有悖君臣之道的,若以其行为结果为“善”(“然后有善者也”)便断其行为合乎道,这是不无问题的。⑩其实,自汉代以来,以“反经”说权,几成主流。(11)下面以董仲舒、郑玄、王弼为例试加说明。
众所周知,董仲舒(前179-前104)“春秋学”多取公羊说,其为《公羊》反经说辩护道:“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不可以然之域。”(《春秋繁露·玉英》)这个“可以然”之说法,意近“道”,旨在强调权必合“道”而后可行,这符合公羊学“行权有道”之立场。东汉经学家郑玄(127-200)注《论语》释“可与共学”章亦以“反于经,合于义”来解释权。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反经合道”说则是王弼(226-249)《周易注》在解释《系辞上传》“巽以行权”时提出的:“权,反经而合道,必合乎巽顺,而后可以行权也。”程颐(1033-1107)所谓“汉儒以反经合道为权”(12),其出典在此,尽管王弼并非汉儒,然在程颐看来,王弼“反经”说当是源自公羊学或董仲舒,故统称为“汉儒”亦情有可原。(13)
对王弼所注《论语》多有汲取的何晏(?-249)的《论语集解》,以及为《集解》作疏的梁朝人皇侃(488-545)的《论语义疏》,对“未可与权”说虽各自有解,但大体上仍承袭“反经合道”说,如皇侃:
权者,反常而合于道也。自非通变达理,则所不能。故虽可共立于正事,而未可便与之为权也。故王弼曰:“权者道之变,变无常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豫设,最至难者也。”(14)
显然,皇疏“未可与权”为“通变达理”之义,以为“通变达理”乃是权的前提。此外,皇疏又引何晏之说,释“权”为“能权量轻重,即是晓权也”,意近权字本义,然而他又引张凭之言,释“未可与权”谓:“又未达变通之权。”(15)可见,何、皇虽理解“权”有“权量”或“变通”两义,但他们却均以“变通”来解释孔子的“未可与权”,未出公羊学“反经合道”的诠释思路。而程朱之所以不满于汉儒的解释,其主要原因即在于:既然“反经”则何以“合道”?(16)
三、程颐“权只是经”
的确,以“反经”说权,极有可能带来一种严重的理论后果,亦即“经”与“权”被完全对置起来,“反经”极有可能变成“离经”,其结果是由“合道”蜕变为“离道”,而“行权”则有可能沦为“权术”。从表面上看,公羊学主张“行权有道”,董仲舒预设行权“必在可以然之域”,王弼以“合道”为“反经”张目,皇侃则以“通变达理”来为行权作合理性论证,这一切都说明汉魏以来的儒者也清楚地意识到行权不能是无条件的,而须以某种“道”作为目标或前提之预设。倘若如此,则反经之“反”似非程朱所批判的仅指“背反”,而是指不拘泥于经典而行方便之权。至于“行权有道”说,看似更为言之凿凿。
然而,从程颐的立场看,汉儒以“有道”来限制“反经”,无非是一种虚设,其“反经”说已不免背离纲常,从而沦为“权变权术之论”,这与儒家坚持纲常伦理的立场就无法调和。程颐的观点见朱熹《论语集注》“可与共学”章,为方便后面的讨论,先将该段注释之全文揭示如下:
可与者,言其可与共为此事也。程子曰:“可与共学,知所以求之也。可与适道,知所往也。可与立者,笃志固执而不变也。权,秤锤也,所以秤物而知轻重者也。可与权,谓能权轻重,使合义也。”杨氏曰:“知为己,则可与共学矣。学足以明善,然后可与适道。信道笃,然后可与立。知时措之宜,然后可与权。”洪氏曰:“《易》九卦,终于‘巽以行权’。权者,圣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权,犹人未能立而欲行,鲜不仆矣。”程子曰:“汉儒以反经合道为权,故有权变权术之论,皆非也。权只是经也。自汉以下,无人识权字。”愚按:先儒误以此章连下文“偏其反而”为一章,故有反经合道之说。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义推之,则权与经亦当有辨。(17)
所引两段程子语,皆为程颐语。关于“共学”“适道”两条的解释,几是常识而无争议(关于“与立”的解释,详见后述)。至于“与权”,程颐首先对“权”字做了定义性描述:“权,秤锤也,所以秤物而知轻重者也。”按以“秤锤”释权或是源自6世纪的字书《玉篇》。其实《荀子》亦释权为“权秤”(《非十二子》),意同“秤锤”。至于“知轻重”,则见《孟子》“权,然后知轻重”(《梁惠王上》)。要之,“秤锤”当是权字本义。
接着程颐对“可与权”进行了解释:“谓能权轻重,使合义也。”质言之,即“权轻重,使合义”这六个字,才是孔子言权之本义。这里,“权轻重”毫无“权变”之意,而是指对于事物的一种判断;“使合义”则表明这种判断须合乎“义”的标准。程颐认为,孔子的“与权”应当就是“权轻重,使合义”之权,除此之外,不能有其他的解释。基于此,程颐批评汉儒“反经合道为权”无非是“权变权术”的变相说法,都是错误的。最后他提出了“权只是经”这一强言式命题,欲从根本上颠覆汉儒“反经”说。不过此说不免矫枉过正,就连朱熹也不得不承认,程颐批评汉儒“反经合道”固然不错,但若以孟子“嫂溺援手”说为据,则经权毕竟有别。当然,朱熹对程颐此说虽有微词,但对程颐的经权观则有根本认同,此容后述。
那么,程颐对“可与共学”章特别是其中的“未可与权”说持何见解呢?为更全面地了解程颐对“与权”的诠释,有必要先对程颐论权作稍详的探讨,因为在我看来,程颐对“未可与权”的解释独树一帜,最接近孔子之本义。首先须指出,程颐坚持认为权就是衡量事物的尺度标准,决不能认同权变权术之说。(18)他说:
权之为义,犹称锤也。能用权乃知道,亦不可言权便是道也。自汉以下,更无人识权字。(19)
朱熹所引程颐语“自汉以下,无人识权字”即出于此。其中,“用权乃知道,亦不可言权便是道也”,显然是对“权只是道”的一个补充说明,显示出程颐并非不了解在字义上,经自是经而权自是权的界线分别,但是此一分别绝不意味着经权两字互不关涉、彼此隔离,而是说“用权”必以“知道”为归宿。他又说:
世之学者,未尝知权之义,于理所不可,则姑曰从权,是以权为变诈之术而已也。夫临事之际,权轻重而处之以合于义,是之谓权,岂拂经之道哉?(20)
末句所言“是之谓权,岂拂经之道哉”,意同上述“用权乃知道”,即权不离道,若强言之,则可谓“权只是道”,即“权只是经”。
上面两段引文,表现出程颐对“权”的最为明确的见解,其中又分两义:一是权“犹秤锤”,一是权须“合义”,即须“知道”而不能“拂经”。前者是权之本义,其引申义便是权衡轻重、明辨是非,基于此,才能保证行权“合于义”,也就等于合乎“经”。故程颐又有“才合义,便是经也”之说,进而对孔子“与权”说提出了重要解释:
古今多错用权字,才说权,便是变诈或权术。不知权只是经所不及者,权量轻重,使之合义,才合义,便是经也。今人说权不是经,便是经也。权只是称锤,称量轻重。孔子曰“可与立,未可与权”。(21)
可见,程颐基于权即“称量轻重”的立场,认定孔子“与权”的权字正是权衡义而非权变义。据此,孔子之意就应这样理解:他欲追寻的是“可以共同拥有权衡判断”之人。显然,程颐的这个解释完全突破了汉儒以来以“反经”说权的传统观点。在他看来,若按汉儒的解释,孔子之说就变成了这样的意味:孔子想要寻找“可以共同拥有权变”之人。
程颐在另处对“可与共学”章有一简明扼要的解释,可与上文合观:
有求为圣人之志,然后可与共学;学而善思,然后可与适道;思而有所得,则可与立;立而化之,则可与权。(22)
最后一句有关“与权”的解释值得注意。“化之”一词,意不甚明,令人联想起孟子“大而化之之谓圣”(《尽心下》)。故可确定“化之”乃属境界语,达此境界者,一切现象的是非对置均可化而不滞、过而不留。而能达此“化境”者必非等闲之辈,依程颐的看法,即相当于“造道之深”者,他说:“若夫随时而动,合宜适变,不可以为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几可与权者,不能与也。”(23)显然,这里所述亦涉及“可与共学”章。至此,程颐的观点已很明确,他清楚“随时而动,合宜适变”乃是“权”之要义所在,这与其“权衡”须“合义”的观点完全一致。按训诂常识,义者宜也,而宜者又有事宜、时宜之分,故宜者并非一定不变,关键在于如何把握“适变”,故权衡当以“适宜”即“合义”为判准,如程子所言“义者宜也,权量轻重之极”(24)。另一方面,既然权衡须合义,则权衡之上必有更高的标准存在,此即一定不易之道(即“经”)。在此意义上,经就相当于“义”,故义又具有统合经权的地位,程颐说:“权之为言,秤锤之义也。何物为权?义也。然也只是说得到义,义以上更难说,在人自看如何。”(25)
权既为秤锤义,故权之本身又有标准义。甚至孔孟经典就是一种权衡标准,例如:“《论》《孟》如丈尺权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见得长短轻重。”(26)可见,权作为尺度权衡,其分量之重,实不容忽视,因为以《论》《孟》为代表的儒家经典之义理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权,为后世提供了“量度事物”的尺度标准。
程颐之后的程门后学亦多能守程颐有关经权的解释立场而不失,限于篇幅,此不赘述。(27)以上我们对程颐的经权说已有了一个较清楚的概观。程颐之所以说“权只是经”,这是因为行权须合义,而“才说义,便是经也”,由此出发,故“与权”之权既非反经亦非权变之意,而必是“尺度权衡”之意。根据我们的判断,程颐对孔子“未可与权”的上述诠释应当是符合孔子之本意的。何以如此说,此容后述。
四、朱熹“反礼行权”
如上所述,朱熹《论语集注》对“可与共学”章的解释仅有一句,即有关“可与”两字的解释,并未对三句四言逐字逐句进行疏解,其中对程颐“权只是经”之说也有保留,认为“权与经亦当有辨”,其依据是孟子“嫂溺援手”说,从中可见朱熹倾向于认为孔子“与权”近“权变”之意。的确,朱熹在字义训诂上向来严格,若从字义上看,朱熹断定:“经者,道之常也;权者,道之变也。”(28)由此,经为常,权为变,则权自然就有应权通变之意。所以,朱熹认为孔子“未可与权”与孟子“嫂溺援手”都表明权与经不可混同,而程颐“权只是经”则易引起误会,他说:
若说权自权,经自经,不相干涉,固不可。若说事须用权,经须权而行,权只是经,则权与经又全无分别。观孔子曰“可与立,未可与权”,孟子曰“嫂溺援之以手”,则权与经须有异处。……伊川说“权只是经”,恐也未尽。
伊川说“权却是经”,却说得死了,不活。(29)
看来,朱熹的立场很坚定,经权有别而不可混同。但是朱熹对程颐“权只是经”并未全盘否定,相反,他甚至肯定“伊川论权非反经之意,则非先儒所及也”,意谓程颐之论权在儒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不仅如此,而且二程以降“诸家论权,皆祖程子之说”(30),表明程子论权之观点在当时道学思潮中已占有主流地位。的确,就朱熹言,他承认权字本义与经相反,涵指变、反常,但他认同的是孟子“嫂溺援手”这一道德领域的行权,却不能认同汉儒以来特别是公羊学系统所强调的政治领域中的权变或权术。更重要的是,朱熹认为在经权之间有“义”及“道”的存在,起着贯穿或统合经权的作用,正是在这一点上,朱熹与程颐达成一致。以下略作分疏。
朱熹曾说“毕竟权自是权,经自是经”,显见这是针对程颐而发,隐含着对“权只是经”的批评,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朱熹的立场便倒向了汉儒“反经”说,故紧接上文,朱熹立即以断然的语气强调指出:“但非汉儒所谓权变、权术之说。圣人之权,虽异于经,其权亦是事体到那时,合恁地做,方好。”所谓“合恁地做”,意指合当做,即行为须合乎所当然之理。在此场合,朱熹更喜用“义”来表述,如:“以义权之,而后得中,义似权,权是将这称去称量,中是物得其平底。”由此出发,朱熹得出了几乎与程颐同样的结论:“权者,乃是到这地头,道理合当恁地做,故虽异于经,而实亦经也。”这最后一句应与“权亦是经”并无二致,只是这句强言式命题须经过义理上的一层转折,即在行权合道的意义上才可这样说。
事实上,程颐何尝不知经权有别的道理,只不过他为反对汉儒“反经”说,不得已而有此强言式命题。对此,朱熹显然能洞穿隐微,故他在言语之间虽有批评,但在原则上并不反对“权只是经”的立场,只是朱熹的义理分疏更细密。在他看来,经权不杂而又经权不离,这才是经权本应如是的关系。由前者看,“权只是经”便不免说得太重,有可能导致“若偏了”的后果;由后者看,汉儒错会了经权不离之关系,故其“说权,遂谓反了经,一向流于变诈,则非矣”。
朱熹对经权有一重要界定:“经是已定之权,权是未定之经。”关键是,经权不仅是观念上的设定,更须置于行为过程中来审视,才能获得真切的理解。朱熹强调正是在行为过程中,“若用得是,便是少他(按,指权)不得,便是合用这个物事;既是合用,此权也所以为经也”。这就告诉我们,经权两义,权不离经,变中有常,权须合经。其中最重要者莫过于权不离经,行权若离经,则非真正的行权;而行权合乎经,则此权即是经。应当说,这是朱熹对程颐“权只是经”的一种论证,而此论证的角度很重要,即将经权置于实践过程中才可说“权也所以为经”。而公羊学赞赏祭仲“知权”,却无视祭仲“逐君立庶”这一具体政治行为在根本上已有悖君臣大义之事实,对此,朱熹也是极为反感的:“公羊就宋人执祭仲处,说得权又怪异了。”(31)并对汉儒说权与程颐说权进行了比较,指出:“大抵汉儒说权,是离了个经说,伊川说权,便道权只是经里面。”意谓程颐本意并不是将权与经对置起来,而是说权中有经,行权须以经为标准。至此可见,程朱在经权观上的立场基本是一致的。
需注意的是,所谓经权不离,权在经中,似乎消解了“经自经,权自权”的区别,将原本属于“变”之权等同于原本属于“不变”之经,但事实上,朱熹之意在于强调,即便在行权过程中,也须考虑是否“合用这个物事”,即应思考是否“合当做”,若“用得是”则行权必“合乎经”。可见,此所谓经又近“理”或“义”的意思,而非具指某种伦理规范(如“男女授受不亲”之“礼”)。由此,在经权问题上,义的问题就凸显了出来。
上面提到程颐释“可与权”,曾有“才合义,便是经也”之说,其中“合义”是关键词。然朱熹以道、义并用来统合经权,如:“道是个统体,贯乎经与权。”“‘义’字自包得经与权,自在经与权过接处。”“经自是义,权亦是义。‘义’字兼经权而用之。”这个“义兼经权”说应当与程颐“合义”说是一致的,只是朱熹对此有更具体的阐发:“权者,乃是到这地头,道理合当凭地做,故虽异于经,而实亦经也。”此处“合当凭地做”便是指“义”。至此可见,权不再是反经或反常之行为,而是“合当做”,即合义之行为,结论是,权只在经里面。显然,以义来统合经权,以使权正当化、合法化,以防其沦为权术,这是程朱理学在儒家经权观问题上的一项理论贡献,实不容忽视。
那么,朱熹对孔子“未可与权”说又是如何诠释的呢?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程朱显示出不同。朱熹由“权自权,经自权”这一经权有别的立场出发,将孔子“未可与权”与孟子“嫂溺援手”视作同义,他说:“‘可与共学’,有志于此;‘可与共道’,已看见路脉;‘可与立’,能有所立;‘可与权’,遭变事而知其宜。”朱熹以“遭事变而知其宜”来解释“与权”,故当有弟子问:“‘可与权’,是‘嫂溺援之以手’”的意思吗?朱熹的回答很肯定:“然。”这就与程颐的解释立场不尽一致,而是以孟子意义上的“反礼行权”之权变来解释孔子的“与权”。然而,朱熹又对“未可与权”做了一个重要的限定,以为圣人才有资格说“可与权”:“‘可与立,未可与权’,亦是甚不得已,方说此话,然须是圣人,方可与权。”
与此相应,朱熹甚至表示“若以颜子之贤,恐也不敢议此”。这莫非说真正有资格拥有权变之能力者唯有圣人吗?这个说法有点奇妙。我们在上引朱熹《论语集注》“可与共学”章看到其引“洪氏”之说,有“权者,圣人之大用”一句,便可明白朱熹对此其实是颇为赞赏的。但是,如果说连历来被称作“亚圣”的颜回都没资格谈权而唯有孔子才能这样说,那么,一般意义上的“嫂溺援手”之权岂非常人所不能为吗?倘果真如此,则“嫂溺援手”便失去了普遍意义。显然,“须是圣人,方可与权”与“嫂溺援手”之权应有区别,前者属特殊的政治领域,后者则属普遍的道德领域,对此朱熹并未作严格的区分,故有必要再作一番分疏。
朱熹曾指出:“所谓经,众人与学者皆能循之,至于权,则非圣贤不能行也。”这里“众人”与“圣贤”的区隔显然不是道德意义上的,因为我们不能说,众人与圣贤由于在德性上存在根本差异,从而决定前者不可行权而唯有后者才能行权。因此,朱熹这样说的理由一定另有所在。按我们的分析,朱熹所着眼的不是德性上的差异而是政治身份上的不同,众人不能像圣贤那般行权的“权”应当属于政治领域,而不是一般道德领域。这也就是“权者,圣人之大用”的旨意所在。当然,朱熹上述解释是否合乎孔子“与权”之本义,这是另一层面的问题,自可另当别论。但是我们应看到,朱熹强调此说的用意却在于对君臣之权的限制。关于君权,暂置勿论,对臣权,朱熹是十分警惕的,他特别强调程颐之所以说“权只是经”,就是因为程颐担心汉儒“反经是权”说将导致“后世无忌惮者皆得借权以自饰”,而能够“借权自饰”者,绝不是一般民众而应是手中握有一定权力的官员或士大夫。可见,在朱熹,权有两义:一则在道德领域,如“嫂溺援手”,是众人所能行之权;一则在政治领域,则非“大贤以上”之圣人不能行之。退一步说,即便是圣人,其行权也是有条件的,“如汤放桀,武王伐纣,伊尹放太甲,此是权也”,倘若“日日时时用之,则成甚世界了”!另一方面,圣凡之间的行权也应有严格区别,如“‘舜不告而娶’,是个怪差底事,然以孟子观之,却也是常理,只是不可常用。如人人不告而娶,大伦都乱了”。这些案例说明,对于政治人物而言,行权也应受到一定的制约而“不可常用”的。
至此,我们终于了解朱熹之论权有一个特殊的政治学角度,故有“须是圣人,方可与权”之说。另一方面,与程颐之释“权”不尽一致,朱熹认定“与权”之权必与经字相对而言,意同孟子“嫂溺援手”之权。而朱熹为圆融己说,他甚至这样解释“可与立”与“可与权”的关系:“孔子曰‘可与立,未可与权’,立便是经,‘可与立’则能守个经,有所执立矣,却说‘未可与权’。以此观之,权乃经之要妙微密处,非见道理之精密、透彻、纯熟者,不足以语权也。”(32)也就是说,“可与立”的“立”与“未可与权”的“权”,恰巧构成对应之词,前者为经而后者为权,前者谓常而后者指变。(33)不得不说,朱熹的这个解释显然过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