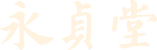内容提要:人性论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古老的问题,也是宋明理学的重要问题。理学的核心问题是“性与天道”,它在探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把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引向了新的高度。理学的人性论是作为本体论的推衍或论证而存在于各个哲学家思想中的,从表面上看,它似乎仍然纠缠于性善、性恶及人性、物性的纷争中,实际上则已突破了这些传统的伦理命题,而表达了哲学家关于人类与自然、宇宙规律与道德准则、主体与客体关系等问题的见解。本文从这一角度分析了王阳明的人性思想及其与朱熹思想的关系,认为王阳明批判了朱熹性、形为二的倾向,将理学本体问题的重点从性理转向心性,把人的身心、知行、道德与精神等概念融为一体,是对儒家传统人本主义思想的一种唯心主义发展。
关键词:朱熹;王阳明;性理;心性
一、逻辑起点的转换
王阳明心学的形成最初是以对朱熹“格物”方法的体验和批判为出发点的。他在运用朱熹的“格物致知”方法进行道德修养时,不只一次地发现这种方法所造成的“心理为二”的矛盾。王阳明曾说:“朱子所谓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穷其理也,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与理而为二矣。”(注:明·王守仁撰:《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见叶绍钧点注《传习录》(商务印书馆,1923年1月版),页112。)这里所谓“析心理为二”,在宇宙观上自然包括了主观与客观对立的内容,但在道德修养论上却提出了如何把哲学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与对社会伦理规范的认识相协调,如何使他们对世界本体的认识与其社会价值观念相一致起来的问题。也就是说,朱熹理学既然要用哲学世界观和认识论来论证封建伦理,就面临着在本体论上调和自然观和伦理观,以及在认识论上统一知识观念与价值观念的问题。这是朱熹理学的重要矛盾,也是王阳明心学所要解决的问题。
朱熹哲学以抽象的客观精神“理”为出发点,把人和物都从这里推出来,以构成哲学体系。此“理”是自然的本质,万物生成和运动的根源,同时也是伦理性的精神本体,封建的“仁义礼智”,最高的真理和道德准则。他以为天下“只是一个理”(注: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6册(中华书局,1986年3月版),页2374。),“理”包容了天、地、人、物,这样,理所具有的自然与伦理、客观与主观的双重特性就给他扩展推衍自己的体系造成了困难。尽管在本体论范围内,他可以用思辨的方法将封建伦理教条强加给天地万物,以为“性即理”,理在与气结合生成万物的过程中,也就把“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性赋予了万物,但在认识和道德修养过程中,他却必须把“理”本体与具体人的思维相结合,才能把“理”变成主宰和支配人行为的实践道德准则。朱熹哲学在把“理”从天推到人的一开始,即把本体论衍为人性论时,就暴露了矛盾。
在朱熹看来,理本身“无情义”、“无计度”、“无形迹”,而人却是有形体、有知觉、有情义、有思忖的,故他用自然观的“理、气”关系解释人性,以推衍天、人关系。他把“理”当作人的道德理性本质,用“气”说明人的生命现象、知觉活动。由此区分“理”与“生”、“性”与知觉,他以为理是“生之理”而不是生命本身,“性”为知觉之理,存在于知觉中,与“心”相即,但本身不能知觉,因而“性”不等于“心”。这样,“性”是抽象的,“心”是具体的,它们之间也包含着“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意味。他说:“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于天之气也。性,形而上者也;气,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气。然以气言之,则知觉运动,人与物若不异也;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得而全哉?”(注:宋·朱熹撰:《孟子集注·告子上》,引自《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10月版),页326。)又:“灵处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注:《朱子语类》第1册(版本同前),页85。)“先有知觉之理。理未知觉,气聚成形,理与气合,便能知觉。”(注:《朱子语类》第1册(版本同前),页85。)
为了说明人性本身即蕴涵着形而上之“理”与形而下之“气”的对立,使天理、人欲不相混杂,朱熹分别了“命”与“性”,“性”与“情”、“才”,“人心”与“道心”的不同。他以“命”为天地之理,即天对人与万物所赋予的抽象本质,以“性”为人、物所禀受于天的具体之“性”。由此,他分“性”为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认为本然之性为人、物未生之本体,而气质之性是人生之后形气所杂的现实人性。“性”是寂然不动的伦理本体,万古不变的教条;“情”是性之发动、心的活动,人之喜怒哀乐情感的显现,恻隐、羞恶、辞让等心情的流露,以及意志、知觉、思维活动;“才”是性的具体表现形式,人的自然素质与先验能力。这样,他就把基于人的心理活动的道德修养过程与指导修养的道德理性观念分割为二。他把“心”分为“道心”与“人心”,以“道心”为出于道德理性的“义理”之心,“人心”为出于本能欲望的“形气”之心,要人“以心使心”,“道心为一身之主,而人心为听命”(注:宋·朱熹撰:《朱子文集·答陈安卿》,引自《朱熹集》第5册(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版),页2919。)。这样,“心”也被分成了“形而上”与“形而下”两部分。
朱熹从“天理”出发对人性及人的精神现象所作的分析有一定合理因素。他看到了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区别,也分析了道德理性、道德观念与道德情感、生理和心理需求在人的修养中的不同作用。但他分割了人的意识现象,忽略了人的认识和修养是一个统一的心理过程,其中知识与情感、理性和感性是交融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人的知觉、情感中有义理,人的形气、视听言动也无时不受理性支配。既然如此,所谓“性”与“情”,“道心”与“人心”又截然分割呢?王阳明正是看到了朱熹哲学在道德修养论方面的这一弊病,因而批评其“析心、理为二”的。
与朱熹不同,王阳明是出于对实践道德论证的需要而去探讨本体问题的。他之所以迫切要求把主观与客观合一,旨在说明:仁义礼智不仅是客观的道德规范、统治阶级对人们的制约,更是每个人发自内心的要求,是人心固有的天然本性。因此,把具有伦理本性的个体之“心”当作宇宙本体,用它来同化封建道德的内容,以便形成修养论、认识论和本体论圆融的体系结构,达到伦理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一致,这就是王阳明对“心、理为二”问题的解决。
王阳明所处的时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都十分激烈,封建伦理教条不仅在下层人民中失去了神秘的权威,即使在上层集团中也不再具有箝制人心的力量。为了安定封建秩序,挽救明王朝于危机之中,王阳明痛感抓住“人心”对于贯彻“天理”的重要性。他的所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亲身感受,以及对世人“分心与理为二……外面做得好看,却与心全不相干”(注:《传习录下》(版本同前),页265。)的批评,正是表达了这种急切心情。王阳明在建立心学体系时对朱熹哲学中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论作了新的调整,他以人为世界的中心,把天地万物都从这里推出去。这样,其哲学的出发点已不再是概括自然与社会现象的客观观念、抽象天理,而是具体的心性,是人的主观道德精神。王阳明剔除了朱熹哲学中与自然知识相关的内容,把“理”的内涵直接限制在社会伦理的范围内,这样既省去了朱熹哲学中从自然观到社会人生问题的繁琐推证,也不必再纠缠于如何把自然之物的认识运用于自身修养过程这样苦恼的问题(如王阳明在“格竹”中所探讨的那样)。他把“理”直接放到人的心中,以便对人的行为发挥最大的效用。
但是,为了达到用世界观论证封建伦理的目的,王阳明在建立心学体系时也同样遇到麻烦。首先,他用来作为世界观基础的“心”是主观之心、个体意识之心,这样的心不仅可以起到维护封建制度的作用,同时也潜在着对封建制度造成破坏的巨大的力量。为此,把天理固有的封建伦理内容与人的心理活动相结合。这是王阳明心学的人性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其次,由于把人心当作世界本体,他还必须说明人的心性不仅是社会伦理本体,同时也是基于自然的知觉思维本性,才能找到人与万物共通的基础,以便把人性论扩充到本体论,建立自然观、认识论与道德修养论统一的心学体系。王阳明的人性论就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展开的。
二、心、性的一元化
王阳明是主张性一元论的,诚然,其“性”已是与心之知觉合为一体的生命之性,这正是他对朱熹分性、形为二论调的批判,但从中亦可以看出他对天人关系,即人性与天道问题的看法。王阳明论“性”,择其要而述之,有如下几点:
一曰“见性。”王阳明说:“性无定体,论亦无定体,有自本体上说者,有自发用上说者,有自源头上说者,有自流弊处说者:总而言之,只是一个性,但所见有浅深尔。若执定一边,便不是了。”(注:《传习录下》(版本同前),页252。)又说:“今之论性者,纷纷异同,皆是说性,非见性也。见性者无异同之可言矣。”(注:《传习录下》(版本同前),页268。)他以为“性”没有一定的格式,古人论性不尽相同,只是所见有浅深,今人论性不同,也只是“说性”,而非“见性”。“见性者无异同之可言”,只有从性的本体与发用、源头与流弊等不同方面看到它们的统一本质,才可谓“见性”。这种“见性”的思想直接驳斥了朱熹将“性”分为“形而上”与“形而下”两截的观点。
二曰“看得一性字分明,即万理灿然”。陆原静曾问:“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是性之表德邪?”王阳明说:“仁、义、礼、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予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之心。心之发也,遇父便谓之孝,遇君便谓之忠,自此以往,名至于无穷,只一性而已;犹一人而已,对父谓之子,对子谓之父,自此以往,至于无穷,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万理灿然。”(注:《传习录上》,页39。)他从天人合一方面论及性、理关系,以为不仅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四端,即使仁义礼智之四德都只是性在道德方面的表现。“性”是不分天、人的。又从“天”、“帝”、“命”而论到“性”、“心”,在用语上似沿袭前人之说,但他把“天”、“帝”“命”与“性”、“心”平列,其实是合天道于人性,无形中降低了“天”的地位,把“天命”与“人性”浑为一体了。他曾说“人心天理浑然”(注:《传习录上》,页29。),也就是这个意思。而“人心天理浑然”也就是他对朱熹理气说在人性问题上的修正。
三曰“性一而已”。王阳明说:“性一而已。仁义礼知,性之性也;聪明睿知,性之质也;喜怒哀乐,性之情也;私欲客气,性之蔽也。质有清浊,故情有过不及,而蔽有浅深也;私欲客气,一病两痛,非二物也。”(注:《传习录·答陆原静书》,页154页。)人性问题是个多层次的复杂问题,既包括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也包括人的存在与思维的关系。王阳明强调心、性的一元化,以思维为唯一本质,把人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全部包容在人的思维特性中。朱熹为了说明善恶的不同来源,而把人的道德意识划分为不同的层次,相应地也把人的心理活动分为性、情、才、质等不同方面。王阳明继承了这些思想,而以此为基础,把道德修养看作一个统一的心理过程。他以“仁义礼智”为先验的道德观念,“聪明睿知”为先天的才质和认识能力,“喜怒哀乐”为先验的心理情感,认为它们都源出一“性”,即人性,人的天性。即使被朱熹看作与“天理”处于对立世界的“人欲”,王阳明也极力从精神的统一性方面来作解释。他以为“私欲客气”虽是“性之蔽”,然其“蔽”也是出于人精神中固有的原因,它是由于人的先天气质不同和情感发用不当所造成的对至善道德的蒙蔽。由此又涉及到他对善恶来源的解释。王阳明认为“善恶只是一物”,原不是在性中有两物相对,他说:“至善者,心之本体。本体上才过当些子,便是恶了;不是有一个善,却又有一个恶来相对也。”(注:《传习录下》(版本同前),页208。)又说:“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子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矣。”(注:《传习录上》,页75。)在他看来,不但“性”无善恶,“物”也没有善恶。所谓善恶只是人心之好恶,而好恶是人心应有之情,“全无好恶,却是无知觉的人”。只要人心“一循天理,便有个裁成辅相”,只要“好恶循于理,不去又著一分意思。如此即是不曾好恶一般”(注:《传习录上》,页76-77。)。这里,他把伦理学的价值原则也完全归于人心,认为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人心的“良知”,“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注:《传习录下》(版本同前),页241。)“是非两字是个大规矩,巧处则存乎其人。”(注:《传习录下》(版本同前),页242。)既然如此,一切社会现象乃至自然现象都可以在人的精神现象、道德意识活动中找到根源,“性”是没有内外的。
王阳明论述“性”的一元性,其核心问题即是心、性的一致和统一;朱熹把性与心分为“形而上”与“形而下”两个世界,王阳明却要在实践道德原则下将二者统一。他以为心即是性,性即是心,这只是心之本体的两个不同方面。心即是性,是从“心”所具有的伦理内容上看:至善是“心之本体”,人人心中都有个“良知”,此“良知”就是衡量一切是非的标准;而性即是心,是从人所具有的生命本质上看:“性”与“生”通,而人生的本质是“心”,“心”是在封建伦理原则指导下思维知觉活动的本质。
关心心即是性,主要应从“心”与“理”的关系上看。王阳明有“心即理”的命题,一方面是继承了陆九渊的思想,同时,也是直接从程朱“性即理”的命题转换而来。程朱的“性即理”把伦理学上人性善恶的问题提到了本体论的高度,同时也就规定了“理”所具有的封建伦理内容。但是这样的“理”是离不开“心”的,也就是说,“理”在道德意识方面的内涵决定了它与人的主观精神的联系,这种联系仅靠朱熹的“理在心中”是不足以说明的。王阳明对“心”与“理”的融合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他提出了“心即性,性即理”(注:《传习录上》,页37。),用先天道德性的内容把“心”与“理”沟通,从而把“性即理”引向了“心即理”。
王阳明的思路是这样展开的:首先,从“理”的内容上看,“理”就是“性”。他说“‘礼’字即是‘理’字……‘约礼’只是要此心纯是一个天理。”(注:《传习录上》,页16。)“‘天理’即是‘明德’,‘穷理’即是‘明明德’。”(注:《传习录上》,页15。)其次,从“穷理”的工夫上讲,他以为“‘格物’是‘诚意’的工夫”,“‘穷理’是‘尽性’的工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工夫”(注:《传习录上》,页26-27。),从而把对外界事物的认识完全归为主观道德的修养。这样,他所说的“理”只是社会政治领域中一个“至善”的极则,也就是人的至善之性。他说:“至善者,性也;性元无一毫之恶,故曰至善。止之,是复其本然而已。”(注:《传习录上》,页67。)但是,他认为至善之本然不在于客观,不在于“物”,而在人,在于人的“心”:“至善即吾性,吾性具吾心,吾心乃至善所止之地。”(注:《传习录上》,页67。)于是,王阳明由“理”转到“性”,由“性”引出“心”,从而得出“心即理”的结论。“心即理”改变了朱熹哲学中天理的客观性质,使“理”成为人的主观道德意识、主观价值原则。王阳明说:“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注:《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页113。)这是他由“心即理”而的得出的必然结论。
但是,把“天理”与人的知觉混同起来,尽管以“良知”标出它的“至善”特性,总是无形中降低了天理的权威。这种倾向早就被朱熹斥之为“通禅”。明儒陈建在《学蔀通辨》中曾多方引用朱熹这些言论来批判王学,并把以“理”或“仁义礼智”为性,还是以“气”或“虚灵知觉”为性当作儒与释,乃至程朱与陆王的分界。与王阳明同时的罗钦顺亦批评王把“性即理”与“心即理”混同。他说:“夫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理之所在谓之心,心之所有谓之性,不可混而为一也。”(注:明·罗钦顺撰:《困知记》(正谊堂全书本),卷一,页1。)又说:“《传习录》有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又问:‘所谓生者,即活动之意否?即所谓虚灵知觉否?’曰:‘然’。又曰:‘性即人之生意。’皆以知觉为性之明验也。”(注:同上,卷三,页1。)“以知觉为性”,这是王阳明批评者对心学的共同结论。诚然,他们抓住了王阳明人性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他对性、气关系的阐述;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性即是心”这一个方面的内容。
王阳明有“气即性,性即气”的命题,表明了他在“心”的问题上把“理”“气”合一的一番苦心。
关于气与生的关系,王阳明这样说:
“生之谓性”。生字即是气字,犹言气即是性也。气即是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气即是性,即已落在一边,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性善,是从本原上说。然性善之端,须在气上始见得,若无气亦无可见矣。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即是气。程子谓“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亦是为学者各认一边,只得如此说。若见得自性明白时,气即是性,性即是气,原无性、气之可分也。(注:《传习录中·答周道通书》,页141。)
又说:
问:“‘生之谓性’,告子亦说得是,孟子如何非之?”先生(王阳明)曰:“固是性,但告子认得一边去了,不晓得头脑,若晓得头脑,如此说亦是。孟子亦曰:‘形色,天性也’,这也是指气说。”又曰:“凡人信口说,任意行,皆说此是依我心性出来,此是所谓生之谓性;然却要有过差。若晓得头脑,依吾良知上说出来,行将去,便自是停当。然良知亦只是这口说,这身行,岂能外得气,别有个去行去说?故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气亦性也,性亦气也,但须认得头脑是当。”(注:《传习录下》,页216。)
他是用性与气的不可分离性来论证性与知觉的关系的。朱熹认为,言“心即理”就是混同了道德之“理”与精神之“气”;以“性”为知觉会使人的行为失去准则,成为“无星之秤,无寸之尺”(注:见明·陈建撰《学蔀通辨》(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卷七,页89。)。王阳明却认为气与性本来浑然一物、不可分离,人的知觉中有义理,知觉本身便蕴含着“天理”。他用“气即性”说明人的精神活动包含着道德伦理,“性善之端,须在气上始见得”,“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即是气”。而又用“性即气”说明封建伦理本身具有精神的能动性,它并不像朱熹所说的只是“形而上”的抽象理性,而是寓于人的生命活动之中:“良知亦只是这口说,这身行,岂能外得气,别有个去行去说?”合而言之,他以为“知是理之灵处”(注:《传习录上》,页90。),是“知”的能动性使得“理”具有可行性,人只要“依吾良知上说出来、行将去,便自是停当”。
王阳明的性、气合一思想,通常认为是直接继承二程的。二程曾说:“‘生之谓性’,性即气,气即性,生之谓也。……盖‘生之谓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注:宋·程颢、程颐撰:《二程遗书》卷一,见《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7月版),第1册,页10。)朱熹以此为程颢语录。但王阳明谈论较多的还是告子。归根结底,他是从告子的“生之谓性”中汲取对“生”的看法,又用孟子的先天道德论加以修正折中的。
告子的“生之谓性”,揭示了“性”的基本意义是与生命现象联系着的。而以生论性,这种认识在儒家人性论中是有传统的。例如汉代董仲舒曾以“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注:汉·董仲舒撰:《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见《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12月版),页291。),汉末荀悦则言“生之谓性也,形神是也”(注:汉·荀悦:《申鉴·杂言下》,转引自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8月版),页206。)。他们都直接把人的身心生来即有之趋向当作“性”。这里的关键是对于“生”的理解问题。如告子主张的“食色,性也”(注:《孟子·告子上》见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81年6月版),页255。),是以人的生理自然为性。但若把人的生命单纯解释为生理需求,就会以为人的知觉运动只是为了寻求生理本能的满足,而社会伦理道德准则与本性无关,是对人性的强制。告子的这种“义外”之说遭到了孟子以来儒家的反对。王阳明也是从这一角度批评告子的。他说:“告子是硬把捉着此心,要他不动”(注:《传习录上》,页64。),“告子见一个性在内,见一个物在外,便见他于性有未透彻处”(注:《传习录下》,页233。)。他以为,若依告子,则人的道德行为不是发自内心的,由此,人的知觉就会失去了道德理性的主宰,便会把“信口说,任意行”都当作因循天性。所以他说告子“不晓得头脑”。但他又认为如果“晓得头脑”,即便说“生之谓性”也无妨。他引用告子的生之谓性”,而把“生”朝着人的主观道德、精神活动方面解释,由此认为人的道德行为是出自天性,知觉运动也只是对内心道德的追求;他以此作为人生命的本质,亦即人性问题的头脑,来与告子的“生之谓性”相区分。他说孟子的“形色,天性也”也是指“气”说,正是这个意思。
王阳明对“性”与“生”的看法,把人的身心、知行、道德与精神等概念包容一体,是对朱熹性理说从“性理”向“心理”伦理论转换的关键一环,也是对儒家传统人本主义思想的一种唯心主义发展。事实上,他对告子的“生之谓性”及孟子的形色,天性也“都赋予了新的含义,这反映在他对“真己”的论说中。为了说明问题,有必要引用《传习录上》王阳明与弟子的一大段对话:
萧惠问:“己私难克,奈何?”先生曰:“将汝己私来替汝克。”又曰:“人须有为己,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惠良久曰:“惠亦一心要做好,便自谓颇有为己之心。今思之,看来亦只是为得个躯壳的己,不曾为个真己。”先生曰:“真己何曾离着躯壳?恐汝连那躯壳的己也不曾为。且道汝所谓躯壳的己,岂不是耳目口鼻四肢?”惠曰:“正是为此;目便要色,耳便要声,口便要味,四肢便是逸乐,所以不能克。”先生曰:“美色令人目盲,美声令人耳聋,美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发狂,这都是害汝耳目口鼻四肢的,岂得是为汝耳目口鼻四肢!若为着耳目口鼻四肢时,便须思量耳如何听,目如何视,四肢如何动;必须非礼勿视听言动,方才成得个耳目口鼻四肢……。汝今终日向外驰求,为名、为利,这都是为着躯壳外面的物事……这视听言动,皆是汝心:汝心之视,发窍于目;汝心之听,发窍于耳;汝心之言,发窍于口;汝心之动,发窍于四肢。若无汝心,便无耳目口鼻。所谓汝心,亦不专是那一团血肉……所谓汝心,却是那能视听言动的,这个便是性,便是天理。有这个性,才能生这性之生理,便谓之仁。这性之生理,发在目便会视,发在耳便会听,发在口便会言,发在四肢便会动;都只是那天理发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谓之心。这心之本体,原只是个天理,原无非礼。这个便是汝之真己,这个真己是躯壳的主宰。若天真己,便无躯壳;真是有之即生,无之即死……。”(注:《传习录上》,页94。)
分析王阳明与弟子的这番对话,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王阳明把人当作封建道德的化身,所谓“为己”和“克己”都只为成一个“真己”,这个“真己”便是封建道德本体。“成己”的过程即是用封建道德理性指导自己行为,做到非礼勿视、听、言、动的过程。
其二,他用心、身关系来说明封建道德本体(“真己”)的作用。所谓躯壳的“己”指人的耳目口鼻之感官和四肢等活动器官。因为人的知觉行为都是发窍于耳目口鼻、四肢,而主导于心的,所以“真己”便是“心”,是它主宰着人的躯壳,维持着人的生命活动,“有之即生,无之即死”。这里实际上把身心之“心”,即作为思维活动器官之心与支配人行为的道德理性之心等同起来了。
其三,他以为人心不专是一团血肉,而是表现为生命的精神现象、道德意识。具体讲,就是使人能“视、听、言、动”的灵能,这个灵能便是性;因此心之本体便是性,便是道德本性。它能支配人的行为,使之向不违“礼”的方向发展。因而所谓“真己”就是“心”、“性”合一的“心之本体”。
其四,他以为“心之本体原只是个天理,原无非礼”,它能主宰人之一身而产生知觉、行为,所以人的视、听、言、动就是“天理发生”的过程;“理”只是“性之生理”,它离不开人的生命,离不开人的心性,也离不开人的视、听、言、动。
王阳明关于“真己”的思想概括了他对人的本质,即人的生命活动与社会伦理本性的认识。与朱熹的思想不同,它不是以抽象的“性理”,而是以具体人的“心性”为基础的。王阳明用一个“真己”来概括心、性,因而在他这里,道德与精神、理性与感性、生命与自然是融为一体的。他把人的知觉乃至生命都归结为精神和心理,并把精神和心理统摄于先天道德性的原则之下,从而把社会伦理性当作人的本质,把封建道德性当作人的天性。
至此,从笔者对王阳明与朱熹人性论思想的比较中,我们亦可以看出宋明理学在“性与天道”观方面的理论进展是从“天”一步步接近于人的,而这,对于后来王阳明心学的发展以及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注:参见拙文:《试论王阳明心学的圣凡平等观》,《哲学研究》199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