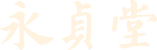掉举:令心于境不寂静为性;能障行舍,奢摩他为业。
不寂静即扰乱,是烦恼的共相。掉举令心不静,即显掉举非唯不寂静,它的自性嚣动,由其嚣掉举动,令俱生的心心所法不寂静,障碍心平等正直住的行舍奢摩他。奢摩他就是止品。
昏沉:令心于境无堪任为性;能障轻安,毗钵舍那为业。
昏沉的自性懵重,皆是昏懵,重是沉重,由昏懵沉重,令俱生的心心所法于所缘境无堪能任持,因此障碍轻快安稳的毗钵舍那。毗钵舍那就是观品。
不信:于实德能,不忍乐欲,心秽为性;能障净信,惰依为业。
惰就是懈怠,不信者多懈怠,故不信为懈怠的所依。不信的自相浑浊,又能浑浊其余的心心所,如极秽的东西,自秽秽他,是故说名心秽为性。
由不信故,于实、德、能,不忍、不乐、不欲,非别实有不忍等自性。若对于染法起忍、乐、欲,体即欲等,不是不信的自体,仅是不信的因果而已。若对于无记法起忍、乐等,但是欲胜解,非与余法为因为果。
懈怠:于善恶品修断事中,懒惰为性:能障精进,增染为业。
于应修的善品事,和应断的恶品事,而懒惰不修不断,是为懈怠:由懈怠故,滋长染法,故说增染为业。
还应该知道,非但于善不精进名为懈怠,即于恶法染事而策励的去作,亦是懈怠,退失善法故。若于无记事策励,于诸善品无进无退,是欲、胜解,非别有体。
放逸:不染净品,不能防修,纵荡为性;障不放逸,憎恶损善所依为业。
纵是纵恣,荡是荡逸,由纵荡故,于染品不能防止,于净品不能进修,就是放逸。因此增长恶法,损减善法。这是由懈怠及贪嗔痴,不能防恶及修善,总名放逸。
慢疑等亦有纵荡性,为什么不依慢疑等上建立放逸呢?这是因为慢疑等虽然亦有纵荡性,不能防恶修善,但与懈怠及贪、嗔、痴等四种比较,则四法障碍精进及无贪等三善根的势用力胜,所以做懈怠等四法建立放逸,而不依慢等。
失念:于诸所缘,不能明记为性;能障正念,散乱所依为业。 对于所缘善等不能明记,名为失念。由失念故,生起散乱,故失念为散乱的所依。痴令念失,故名失念,所以失念以痴念为体。 散乱:于诸所缘,令心流荡为性;能障正定,恶慧所依为业。 流是驰流,即散功能义;荡是荡逸,即乱功能义。散乱的自性躁扰,令俱生的心心所法流荡,于所缘法心不能安住,发生恶慧,所以能障正定,为生起恶慧的所依。 掉举与散乱的作用有什么差别呢?掉举是令俱生的心心所于一种所缘境上解数转易,即一境多解。散乱令心心所易缘各别境,即一心易多境。易解易缘,义成差别。 不正知:于所观境,谬解为性;能障正知,毁犯为业。 对于所观,非是迷暗,而是错谬邪解,名不正知。由不正知多发恶身语业而毁犯戒等,故论说毁犯为业。知即是慧,但由痴故,令知不正,名不正知,故以痴慧两法合为自性。 以上八种,名八大随烦恼。 上来已说二十个随烦恼的体相业用,但在经论中所说的随烦恼,并不止这二十个,如贪、嗔、痴等,邪欲、邪胜解等,趣向、前行等,都名随烦恼。 既有多种,为什么这里只说二十个呢?这有三种意义:(1)简别非是根本烦恼,显其唯是随烦恼。贪等虽然是随,但非唯是随烦恼,所以不说贪等。(2)显其唯是染污。即简别邪欲、邪胜解等,及不定四种,虽然是随,但体通三性,非唯染污,所以不说邪欲等。(3)唯粗动起。趣向、前行等虽亦是随,但行相微细,不是粗动,所以不说。具足这三义,是故唯说二十,不更说余。 又其余的随烦恼,或是这二十种的分位,或是这二十种的等流,皆不出此二十种可摄。如邪欲、邪解等,依不信等分位假立:如愤发等,即忿等同类;趣向、前行等,依无惭等分位假立。由此可以知道,有这二十种随惑,就可以摄尽一切所余的随烦恼,所以说二十种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