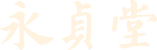庄子的思想在当时勿庸置疑带着些许反动色彩(此乃笔者浅见,如有不同意见,欢迎批评指正),例如“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太尖锐、太深刻、太恣意,亦因此不被各路诸侯所采纳,尚幸他一不求位高权重,二不求锦衣玉食,于是乎依旧做他的漆园吏,依旧著他的《逍遥游》,依旧藏身于陋巷之中,咀嚼着那口饿不着撑不死的俸禄。庄周不若孟柯斗志昂扬地游说诸侯逞尽辩才,“他只在僻处自说”(朱熹答问是云)一径任满腹经纶跃然纸上,任才华横溢细水长流。
历史之流宛如滔滔江水,颇有一泻千里、永不回头之势。奴隶制的西周绝迹于诸侯割据的滚滚烟尘,继之是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尔虞我诈、混战厮杀——大一统前的四分五裂是这方广阔而灵秀的土地在重生前最后的阵痛!
庄周并不是在这场撕心裂肺的阵痛中唯一挣扎的人,他能够在最终潇洒地淡出而不是狼狈地逃遁是我最初对他产生兴趣的原因之一。他曾用一只环来比喻社会,说人世间的一切冲突搏杀、你死我活、血溅泪洒皆在环上进行;环上的任何一点都可能成为斗争双方的立场;如你不想有危险,就只能悬浮在圆环的空虚处,环上的是非,你不必参与——对事物的演化,既不应去推动,也不应去抵制,最好是顺其自然。当时觉得这样的观点太消极、太圆滑,不像大丈夫所言。看过“文景之治”,才发现:对于没有太过丰厚物质积累的社会而言,无为而治似乎存在得更为合理。
有时觉得庄周难免是有些自相矛盾的。他一生渺看世事若过眼云烟,又时而对世情冷暖出言批驳,词锋锐利毫不姑息。庄周一次见梁惠王时身着麻布长袍,襟上补疤,提脚跨上阶陛时,袍带和鞋带都挣断了,惠王问:“庄先生为何如此窝囊?”庄周说:“不是窝囊,贫穷罢了。读书人有抱负没法施展,那才是真窝囊。读书人窝囊,皆因生不逢时,正如鄙人。你看那跳跃在树梢上的长臂猿,让它栖息楠梓樟一类的乔木林,攀缘高枝,往来自如。若斩尽乔木逼它逃入钩棘臭橘一类有刺的灌木丛,行动躲躲闪闪,一身战栗,难道是抽筋断骨了吗?当然不是。处境不妙,无法施展自己的本领而已。现如今,上坐昏君王,下立乱宰相(惠施),有抱负的读书人夹在中间,要不窝囊,谈何容易!”
如此这般的措辞,梁惠王自然不敢恭维,这大概也就是才高八斗的庄周为什么捞不到一官半职的原因了。
我又觉得庄周难免是有些无辜的。年轻时的才华外溢、不知韬晦竟曾引得知交惠施彻查梁国都城三昼夜搜捕之,只因担忧庄周要抢他相爷的肥差。惠施永远都不会相信——庄周只是基于一份真挚的友情、一腔念旧的热情,才远道赶来的——很久不见,想看看朋友——仅此而已。
诸子百家,缘何独独钟情于他呢?
也许是因为……他为人够傲,损人够酸,文章够辛辣,文采够光芒。的确,他活得不够四平八稳,活得不够风光煊赫,但是,我要说,他活得够恬淡、够畅然、够舒逸、够内涵、够浪漫。灼人的烈焰是他的内核,绝对的洒脱是他的内在,嶙峋的怪石是他的风骨,碧空的游云是他的情怀!
论忠君爱国,他不如屈原——前者尽己之能辅佐怀王,受诽谤遭流放仍与楚国誓同生死——而庄周则譬如一羽散居在山林的野鹤;论劳苦功高,他不如孔子——前者历尽坎坷周游列国,虽真知灼见不为所用仍兢兢业业教书育人——而庄周则恰似一尾徜徉碧水的游鱼;论攻防之道,他不如孙武——前者尝言论战精辟缜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而庄周则全然一位闲庭信步的隐士;论经天纬世,他不如韩非——前者的“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波及中国历朝历代,一部《韩非子》应现于秦始皇的“履至尊,治六合”——而庄子,除去汪洋恣肆的锦言妙句之外,似乎对后世谈不上什么大的影响与震撼。
但庄子就是庄子,他尽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存在。他不刻意去度量规划旁人,自然也不希望旁人多留意瞩目他。优游自在淡泊名利隐于江湖,甘心寂寞出世脱俗匿于荒野。不谋一官半职,不求功名利禄,不守俗礼陈规,不食人间烟火——这就是庄子,这才是庄子呵。
庄妻死后,庄子非但不悲不恸,反而拍击着瓦盆吟唱着歌儿。这样的他,令我想起了几代之后提酒挟琴前去吊唁阮籍亡母的嵇康。庄周的简唱陋吟虽不比《广陵散》,不也是一种无比真诚的悼念逝去生命的方式吗?!
我没有深厚的资历去细审庄子的生平,也没有充沛的精力去研读庄子的书著,更没有惊人的勇气和卓越的能力去庄子生活过的每寸土地对现有的关于他的卷宗一一详作考证。我只能立足于几千年后的今天,借着有限的资料,淡淡地解析一番。
庄子是永远也解析不完的,这点我深信不疑。最后,我想用一句话来结束我的文章——“诗的婉约,哲的彻悟,尽现于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