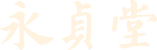杨帆 饰 梁思成
标题 专访昆曲大武生杨帆:不要感叹昆曲知音太少,我们要保质保量完成本职工作
昆曲舞台上,他是《夜奔》《单刀会》《千里送京娘》《华容道》里的大武生,完美演绎北方燕赵男儿的豪爽仗义;生活中,他文质彬彬、温文尔雅,北方昆曲剧院大武生杨帆结缘昆曲已有40多年了。在最近上演的原创大型昆曲《林徽因》中,他饰演梁思成,这是杨帆昆曲舞台生涯中遇到的第一个知识分子形象,如何以古典昆曲演现代戏、现代人,准确找到角色与自身具有的共同点是他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我必须在舞台表演、形象气质上无限接近人物。”
杨帆做过导演、演过话剧、拍过电影,最终还是“留守”昆曲舞台,从懵懵懂懂入行,到与昆曲厮守难分,多的是对昆曲艺术的历练积累,多的也是对昆曲舞台的无限眷恋,多的还是对昆曲艺术传承发扬的重任与担当。说起恩师侯少奎先生,杨帆记忆深刻的是老师细心严格的艺术指导,以及温暖无私的身心关爱。“上一辈艺术家对艺术的传承,对后辈的教导是纯粹而无私的。”
1982年入学北方昆曲剧院至今,杨帆学习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都与这个艺术殿堂密不可分。他满怀深情忆起往日大伙儿围在一起排戏、说戏的情景,“那是一种家的感觉”。昆曲艺术几经起落浮沉,杨帆说,他并不担忧昆曲的没落与无人问津,“昆曲的节奏和欣赏角度,不是所有人都会喜欢的,不要感叹知音太少,这不是我们需要感叹的,作为昆曲人,我们首先要保质保量完成本职工作,对喜欢昆曲的观众有交代就够了。”
昆曲舞台上的“梁思成”
中华网:您在《林徽因》中饰演梁思成,您如何理解这个人物?为了演好这个角色,您做了哪些准备?
杨帆:这部戏是现代戏,要演的是当代人,在形象气质、舞台表演上要能够让观众看到人物的影子。我阅读大量的书籍、看图片等,做了一些对梁思成先生的了解。上个世纪20-30年代,正好是他们风华正茂的时候,年轻又有学问,在当年来说是精英阶层,从小家庭生活优渥,又受到了西方的教育。在李庄,他们行路困难、生活拮据,身体上又有病痛的折磨,但多大的生活落差对他们来说都不重要。他们骨子里的民族气节,强大的信念、坚韧的品格,深深打动着我。
文字提到他第一次软弱是在和当时北京市长要求保留北京城的时候,他失声痛哭,他的恸哭是痛彻心扉的,坚持保留老北京建筑。看到这里我很感动,作为一建筑学的专家,他具有的前瞻性,他对文化的保护与坚守,他的哭泣不仅仅是为了建筑,更是为了民族文化,对于梁思成先生,我充满敬佩。
中华网:您在塑造这一角色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是什么?
杨帆:首先,年龄化是贴近舞台的关键,我已经50多岁了,要演一个20岁左右的人,对我来说,外部形体既要表现出梁思成先生年轻的状态,但又不能显得太过做作。在他们设计国徽和纪念碑的阶段,梁思成先生不管是从学识上,还是从待人接物的状态上,都更沉稳了。用说话的语速、唱腔的声音、走路的台步,去表现一个很成熟的男人,同时他也是一名坚强、坚定、有主见的知识分子,没有了学生时代的彷徨。我在演绎时不能表面地去表现他多么有气质、豪言壮语等,梁思成先生的性格内敛、温文尔雅,这种内化的东西很难表演,我试着找到外部形体的一些动作,找到其特定的姿态去塑造,但抓人物内心的时候,要如何体现呢?尤其是戏曲舞台,和影视又不同,电影可以将镜头推到眼部,通过眼睛或语言去表现,但戏曲舞台表现人物内心,既要带有舞台的表演形式,又要带有韵律性,还要自然适宜不过度夸张表现,梁思成是我目前为止碰到的最难演的一个角色,在平时排练中,我不断揣摩。
想学戏,得吃苦
中华网:您是如何与昆曲结缘的,在您的从艺之路上,有哪些记忆深刻的事?
杨帆:北方昆曲剧院1979年复建院,当时人才匮乏,1982年招收了30个学员班的孩子,当时上戏校有一些优厚条件,一个月25斤粮票,武戏有30斤,每个月还有12块钱的补助,一年有两套练功服。1982年,我11岁,进入北方昆曲剧院学员班,当时是团代班的形式,我们就住在剧院里,日常和演员同吃同住。眼看着老师、师兄师姐们每天排练,随时都能够学习,在练戏时老师会说“孩子,你给我走一遍看看?”因此,我们得到的不仅仅是一名老师的帮助,很多老师都会为我们说戏。
我当时个子比较矮,按照老生招进去,过了半年,老师说我个子太小,改唱短打武生。头半年拍群戏,半年之后恩师侯少奎就教我学《夜奔》了,当时侯老师在舞台上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他白天教我们,晚上演出。教小孩儿很难,得一遍一遍教,侯老师待人非常和善,讲戏时从来不急。学戏是真苦,但咬牙也得坚持,想学戏,得吃苦。我们这一波从事昆曲的演员们对昆曲美背后的残酷是了解的,只有经历过这种残酷,才能真正地把美带给别人。
老话讲“无技不成戏””戏曲里面有很多是技艺的表现,翻跟头、打靶子等,要通过程式化的表演来展示我们对戏曲的特殊理会,得靠身体来表达,因此身体必须锻炼到柔练、敏捷,才能走得漂亮,飞脚才能打得高,别人在一分钟打完,我可能30秒内打完,才能让观众目眩神迷,夺得掌声。这不是说一说、讲一讲就能做得到的,得付出血的代价,为什么现在的孩子出不来名角儿,不苦练能出来好跟头吗?能出来好角儿吗?现在武戏演员太匮乏了,全国戏曲界的武戏演员数量都下滑,青黄不接。一方面心疼他们,另外一方面基础打的不瓷实,我们那些老演员,刘国庆老师、曹保平老师50多岁跟我们一起在舞台上演出,摁手一翻七八个蹶腰,真是了不得。

侯派武生的特点
中华网:请您讲一讲昆曲大武生的表演艺术特点?
杨帆:武生分得比较细,短打武生、箭衣武生、长靠武生,还有猴戏的武生,很多人问武生为何叫大武生?这个行当不单单对文武戏有要求,同时对演员本身的素质也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又有嗓子又有表演。比如锤,别的戏拿锤不撒手,我们更多时候走的是样式、做派,要求稳、准、狠。侯派最早传承于京剧的尚派,杨小楼先生是同门师兄弟,武生的归类,从他们开始,以前昆曲很多的剧目,武戏的角色都是由老生来扮演,嗓子都不错,但是在演武戏的时候,缺乏武将的豪迈、刚烈,比如关公,最早是两个行当扮演,一个是老生,一个是花脸,慢慢地这个戏在侯派这儿打响,由武生来扮演,武生不像老生那样文文邹邹,有武将过五关斩六将的杀伐决断的感觉,但又不像花脸,一般花脸有时候架子太大,在扮演人物细腻的地方因为行当的缘故,导致其不太能够擅长表演人物细腻的心理变化。侯派武生表演多了一份潇洒和灵动、豪迈和慷慨。
对很多武生演员来说,侯派既很他们希望学习但总是无法达到的门槛儿,现在全国一些剧团也出现了很多条件不错的人才、好苗子。有了年轻演员的人才储备,侯派武生应该能够一直传下去。
戏曲是演员本位制
中华网:除了在舞台上表演,您还担任戏曲、戏曲电影、话剧导演,您曾参与执导戏曲电影《红楼梦》,网络短剧《门萨的智斗》,话剧《教育就是兴国》,昆曲《关汉卿》《西厢记》等,请您谈一谈做导演的感受,您在执导一部戏的时候,看重的是什么?
杨帆:做导演太不容易了,身为导演,首先站的位置不一样,导演是剧本的解构者、解读者,同时又是剧组的领路人,不单是从精神上还是体力上,都需要有极大的付出。做导演是很幸苦的事,从某些方面来说,在舞台上展示自己和在幕后默默付出,我可能更倾向于舞台。作为导演,我接触了不少话剧、电影、电视剧,我的体会是做导演,文化修养是第一位,戏曲导演要特殊化,要懂得更多,锣鼓、音乐、唱腔等,如何设计演员在舞台上的行动,从某些方面来说戏曲导演的挑战性更大。
看话剧、电影,观众会首先问导演是谁?剧本是什么?但看戏曲,大家首先关注的是谁来演,第二是剧本,第三才是导演。戏曲最早是没有导演的,戏曲是演员本位制,舞台上的一切都是围绕着演员进行的,只有演员才是吸引观众眼球最终的执行者。
谁都可以执导戏曲的结果就是,戏曲要么变成歌舞剧,要么就是奇幻的舞美和灯光展示,连音乐都带着主旋律,那么演员呢?其实音乐等这一切都是辅助演员表演的。观众来看的就是戏曲演员的唱、念、做、武,看他如何体现人物,我们看很多版本的《杜丽娘》,根本不看谁导的,而是看谁来演,杜丽娘和柳梦梅是如何表演的,“山桃红”唱得如何,舞美什么的都是次之。
传统的魅力是永恒的
中华网:在《夜奔》《单刀会》《千里送京娘》《别母乱箭》《夜巡》《义侠记》《华容道》《麒麟阁·三挡》等经典传统戏中,您喜欢的是哪几部,为什么?
杨帆:《夜奔》《单刀会》《送京娘》这三出戏是侯派最典型的经典折子戏,我演了20年,体会到传统折子戏带给我的魅力,每一次演都能感受自己气息和乐队的配合,和舞台上所有演员气场的融合,是很过瘾也值得留恋的。这些年昆曲排了很多的新编戏,真正留下的有多少?这些传统折子戏,演了上百年,如《单刀会》演了500年。这三部戏,我从小学到现在,依然在唱,观众能在经典戏里,看到历史,看到戏曲真正传承的文化。昆曲最早的是南北曲,魏良辅以昆山腔变为昆曲,当时也是清曲,击节而歌,还没有带舞台行动,《浣纱记》才是真正在演戏。传统的魅力是永恒的,历久弥新,怎么演都不过时,传统戏的程式化已经达到了后人无法超越的地步,我们的脚步、眼神、指法、动作真的已经形成了极高的规格与规范,你不能动它,因为你动它,不可能会比它更好,这些就像教科书似的。

杨帆在《千里送京娘》中饰赵匡胤
中华网:《夜奔》是您的第一出戏,当时学习时记忆深刻的是什么?
杨帆:学《夜奔》的时候,我是最差的一个,个子矮身体又比较软,不够硬实,彩排的时候,师哥身体底子好,侯老师就说“这孩子身体又弱”,在彩排的头天,侯老师拿一个小饭盒来,里面有酱牛肉,说“吃肉长劲儿”,其实那个年代老师对待学生不单单是学生,还把他看成自己的孩子,他们觉得徒弟也是剧种的未来。
那时候彩排连其他行当的老师都过来给我说戏,现在觉得一个旦角儿演员,怎么能给武生说戏,一个普通的学员班的彩排,老师们都来看,参与指导,我很感动,剧场就像家一样,这种氛围也使得我们这一波的年轻人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尤其是昆曲人之间的互相扶持与无私关怀。现在剧院有时候要彩排,我希望大家都来看,比如今天哪个年轻演员彩排了,不止这个行当,别的行当也都来看。
中华网:您在传统戏、新编现代戏、昆曲当代戏、话剧中塑造了大量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您喜欢的角色是哪个?
杨帆:新编戏《飞夺泸定桥》里面的首长是我印象最深刻的。2000年,剧院复排了一次第二版的《飞夺泸定桥》,这个戏在我们剧院60年代初就排过,有些场合也会拿出来演,我当时已经在里面开始演戏了,演的是炊事班长,那时候身材比较肥胖,看红军连长和首长很羡慕。2016年复排,我终于演上了梦寐以求的首长。这部戏承载着北昆的精神,几十年了从六十年代到现在,比我的年纪都大,这部戏也让我体会到昆曲的传承,能看到一个剧院的传承,领会到老一代艺术家和年轻一代之间的纽带。因为年龄差异,我们平时可能和很多老师们的接触不是很多,但在排练这部戏的时候,很多老师都被请回来,老师们岁数很大了,但说起年轻时候的事儿,都意气风发,让我们很感动,老师们一辈子扎扎实实地搞昆曲,让我们很敬佩。

杨帆在《飞夺泸定桥》中饰红军指挥员
观众是昆曲真正存活下去的依据
中华网:你认为当今时代的昆曲,和之前相比,变化在哪里?
杨帆:80年代我开始学戏的时候,一昆曲无人问津,二是昆曲京剧化,那个时候京剧是国粹,别的剧种都学京剧,慢慢地很多剧种就同质化了。
现在昆曲越来越成为当代观众眼里可以和京剧比肩的剧种,昆曲在大学校园很受欢迎,很多人了解到了昆曲,欣赏昆曲文本的文学性、观赏性。很多年轻人走进剧场,觉得看昆曲也是一件很时髦的事。3年前,我们去武汉戏码头带队演出,特意问了剧场人员,当时有昆曲、京剧、徽剧、汉剧、粤剧,得到的消息是,北昆的票买了900多张,而且整个观众年龄段非常靠前,很年轻。
观众才是昆曲不搁在博物馆,真正存活下去最大的依据。如何让昆曲产生真正生存下去的动力,是观众,是年轻观众,所以那次让我有很大的信心,昆曲不单单是因为申遗之后受到国家的重视,也被广大年轻观众所了解。这两年北方昆曲剧院做了一些探索,“不到园林不知春色如许”戏迷培训班,只招收30几个人,但是有300多人报名,而且都是年轻人,这对剧院来说, 300多人就可能变500多人、1000人,这些都是走进剧场的基础。今年8月份,我们举办了昆曲夏令营,去了很多人,观众开始认剧院和演员,想和最好的老师学昆曲。传统古老的戏曲越来越被当代人认知。
中华网:您如何看待戏曲艺术的市场化?
杨帆:戏曲市场化任重道远,不能一下子就推向市场。2001年昆曲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后,有改观,但昆曲的市场普及率、支持率还不够高,对这个剧种,国家的支持还是必要的。昆曲作为百戏之祖,有那么高的艺术造诣,可以作为国家的文艺名片,有时候不能过多考虑经济效益,国家对文化的保护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现在因为一些现实原因,比如对时间的限制,有些传统剧目得一遍一遍修改、删减,从某种角度来说,是一种损失,会对整个剧造成破坏。
戏曲需要寻找更多与年轻人契合的点
中华网:现在生活节奏快,您觉得如何做才能让有慢节奏的传统昆曲走向更多的当代青年,为他们所接受并喜爱?年轻人欣赏昆曲的建议。
杨帆:学什么都需要引导,老师的引领,老师得告诉他什么是好听的,戏曲缺乏让大家了解的渠道,虽然现在做了很多努力,还要需要继续做下去。戏曲和现实生活有脱节的地方,我并不担心戏曲会灭亡,随着人的年龄段的变化,当他沉下来的时候,会听戏曲的词儿,看看词儿是什么?比如昆曲文本曲牌是宋词,“原来姹紫嫣红”,多好听。
中华网:您除了演、导之外,也致力于昆曲的推广工作,在昆曲在当代的传播普及方面,您的建议是什么?
杨帆:现在流行中国风,穿汉服,年轻人应该受受戏曲的熏陶,站有站姿,比如旦角儿走路上身也不动,都是有规矩的,身体的造型感和仪式感,能锻炼人的气质。戏曲演员的状态不一样,剧种和剧种演员的状态也是不一样的。昆曲和当代结合,需要寻找更多与年轻人的契合点。

杨帆在《荣宝斋》中饰殷杰
昆曲的普及推广要有针对性,孩子的理解能力从某些方面来说偏弱,尤其是一二年级,对于昆曲的推广,应该在大学阶段给予更多的力度。大学生的思想、身体已是半个社会人,以后走入社会,可能会离开了昆曲,忙于生活,但是慢慢地,还是会回来的。昆曲的节奏注定只适合一部分人欣赏,不要感叹知音太少,这不是我们需要感叹的,首先作为本职人员,我们要保质保量,提高自身的素质与剧目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