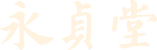吃闲茶是老成都大、中、小茶铺的普遍现象。然而,真正反映了当年社会尝尝众生相的,还是那类遍布街头巷尾的中、小茶铺。
三十年代初,我开始跟随父亲坐茶铺,每天晚饭后,他带我到离家只有一条多街的“第一泉”吃茶。泡一碗茶,占两把椅子,他吃茶,我面前摆一堆花生。当我把花生吃完便沉沉欲谁了。等他茶瘾过足,我巳进入梦乡,父亲只好把我背回家去。久而久之,我也成了一名“茶客”,耳濡目染,印象殊深。这家茶铺不大,双间铺面,摆了三十多张桌子,后堂的飞来椅外,是一涨大大的池塘。这里还是当地抱哥组织“莲泉公”的“据点”。每天一早一晚茶客盈门,四周烟雾弥漫,到处闹闹嚷嚷,每逢一位“头面”人物光顾时,凡是认识他的都得点头、躬腰,争着付茶钱有的人竞争得面红耳赤。头冒青筋。好在堂位经验丰富,熟桧人情世敌,择“优”而取,大家满意,一声“道谢了,下次再惠!”足可平息纠纷。茶铺又恢复原状:咳嗽的,摆龙门阵的,喊“掺开水”、“带随手”的,叫卖瓜子、花生、纸烟的,此起彼伏,一切是声音的流动。
劳累一天的手工作坊工匠和做罢小生意的,年复一年地人茶铺里休息,龙门阵大家摆,茶各吃各。有的习惯闭目养神,听到会意处搭白两句;如遇“颜色不合”,不妨端起茶碗换个桌子,别人也不会多心。还有一种吃闲茶的,成天没事干,一碗茶坐上大半天,堂值照样轻轻揭开盖子掺开水。临时要离开,给堂倌打个招呼“留一下”,或者抓几片茶叶放在茶盖中间,那些专门吃“加班茶”的也不会去动它。
吃讲茶(又叫“讲理信”)是老成都人日常生活中发生纠纷的一种调解办法。每逢茶铺里出现吃讲茶的,看闹热的最多,‘扎墙子”的不少,而最忙的要数堂倌了。茶碗一摞摞地抱来摆开,见坐下来的就泡一碗,手脚之麻利令人叹为观止。吃讲茶关键在于当事双方各自“搬”来什么人。如果“后台”硬肘,即使无理也会变得“有理”;如果地位低于对方,有理也说不清楚,那只好认输把全部茶钱什了。也有双方势均力敌,僵持不下的,出面的“首人”,便采取各打五十板的办法,让双方共同付茶钱;或者他装起一副准备掏钱的架势,意在“将”双方“一军”。此刻,双方只好“和解”了事。偶尔也有一言不和,茶碗乱飞,头破血流的,最后赔偿时,历年打烂的茶碗、桌椅,都一齐算到“输理”者账上。有件事至今未能忘怀:一邻居的女儿被一个小老板调戏,她的父母忍不下那口气,找对方吃讲茶。因对方人多势众,“首人”断了“弯弯理”,先责怪两老人“教女不严”,然后要他们付茶钱。对方“扎墙子”的趁机起哄。嘲笑,弄得两老人无法下台,一个当场气昏,一个蔫弹地付了茶钱。那年月,歪人到处有,惟独没有平民百姓“讲理”的地方!5 吃书茶(又叫“听评书”)是老成都人的文娱活动之一,小茶最为常见,花钱不多.既吃茶又饱耳福。每逢下午或晚上,一向冷落的茶铺变得闹热了。中间摆开一张特为说书先生设置的桌子,和一把靠背高脚椅子.一张黑漆粉牌上写着他的大名和书名。眼看茶客满座,说书先生轻轻咳嗽几声,抓起桌子上的“界方”连拍三下,堂值随之吆喝:“开书呷.各位雅静!”顿时,堂里鸦雀无声,只听他徐徐道来。父亲喜欢听评书,后来便转移到一家小铺吃茶了。寒、暑假期间,我常常跟贿他去听评书,久而上瘾。评书除了座上客之外,还有不少站在茶客身后充当外围,俗称“战(站)国”的。这是一批不愿花钱的热心听众,以衣衫破旧卖劳力者居多,也有少数年龄与我差不多的,每当说书先生中途‘闸板”下来收钱时。他们便纷纷离开,又开始说的时候陆续围拢。尽管他们并不受欢迎,然而,如果没有这批“捧场”的忠实听众,那吃书茶的气氛将会大打折。夏天,座上客回头皱眉,他们尴尬地朝后退;冬天.他们充当别人的“肉屏风”。吹得鼻子通红,仍旧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洗耳恭听。多年以那景象还历历如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