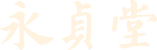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乱机就空袭我大后方成都,从此,蓉城市民开始了历时几年、疲于奔命的“跑警报”。城外纷纷开辟了“疏散区”,不少因陋就简的茶铺也随之出现。其中,以新南门外府河两岸的茶铺最多,也最为闹热,稍具规模的茶铺北岸有四家,南岸有两家;而两岸又各有一家占优势的大茶铺,形成对比鲜明的茶文化现象。
北岸那家大茶铺名口名叫“江上村”,是李劫人长篇小说《天魔舞》写到的“花园茶铺”。它紧靠河边,位居上游,占地面积相当宽阔,是不可多得的好“口岸”,除经营茶铺外兼营“竟成日”餐厅。当年的“江上村”环境幽雅,风物宜人,既有茂林修竹掩映又有河流可供观赏,花草葱笼,游廊环抱,令人流连。比之于“郊外第一公园”的“雷神庙”(望江公园前身),有过之无不及。茶铺分两重:前面的茶座露天摆设,一律的四仙桌和靠背竹椅;后而游廊的茶座全是漆成偷油婆色的木桌木椅,给人以整洁之感。逢上好天气,前前后后,座无虚席。如遇“跑警报”,更是人头攒动,闹闹嚷嚷。抗战前,妇女尤其是青年妇女不能在茶铺抛头露,而这里却有不少衣着时髦的女青年和男士们平起平坐,或品,或交谈,或看书,或围坐打扑克,欢声笑语,引人注目。和城中的大茶铺一样,卖瓜子、花生米、香烟的小贩多得难以胜数。又擦皮鞋的蓬头少年,穿梭般地往来于茶客间,只要看见穿皮鞋;总是把吊在肩上的木箱敲得特别响,直到把脚伸向他为止。有出租报纸杂志的,只花很少的钱,便可阅览大半天。每天午四点左右,照例有一个提起兜兜卖金约花生、五香盐胡豆的中人出现,那叫卖声喊得有板有眼,吸引着众多的茶客,一个个购买,用以住茶,别具风味。常在少城公园茶铺以“看相”为的,几乎天天在这里露面:他们穿着晒血浸了的蓝布长衫,衣上挂着一面写上“麻衣相法”的小木牌,默默地在茶客旁边摇摆去,有的还轻言细语地说:“看相不?看妻财子禄,负责说。不准不要钱!”
与“江上村”茶铺对着干的,是南岸桥(今成都汽车中心站一家草盖屋顶、周围用篱笆作墙壁的大茶铺。它是当地一个哥“舵把子”开设的,虽然等级较次,卫生条件也差,但老板的花样多,其生意之兴隆并不在“花园茶铺”之下。花样之一,是雇年轻的女茶房送热水毛巾(另外付钱)。当茶客需要(或根本不要)擦汗时,只做个手势或喊一声,那热水毛巾便凌空迎面飞个别轻薄茶客以此为乐。专找女茶房寻开心:挤眉弄眼做怪打情骂俏动手脚。因此这种花样太不像话,不久便自动消另一花样是邀来说唱艺人表演金钱板、茶鼓、竹琴、口技、清节目。每当午后,那家茶铺锣鼓喧天,弦歌不绝,两百多把椅坐得满满的。茶客以中、下层市民占绝大多数,极少的女茶客老太婆,他(她)们到这里来主要是听演唱,有的宁肯买一碗“玻璃”(白开水),也要舒舒服服地坐下来听一段曾炳昆的口技,李月秋的清音。一段时期,清音《断桥》中“一把手拉官人断桥坐---”,曾在那一带风靡一时,几乎家喻户晓。然而有人却斥为“下九流!”说是“光听了都要生疳疮子!”尽管如此,这家茶铺的盛况却几年不衰。
抗战胜利后,新南门外的几家大茶铺逐渐冷落:“江上村”因故歇业,“竟成国’迁回青石桥南街原址;南岸茶铺的说唱艺人先后奔回城里茶铺另谋生路。曲终人散,一派萧条!
斗转星移,人世沧桑。昔日的许多大大小小茶铺,早巳成为历史陈迹,当年形形色色的茶铺众生相,也仅仅如梦似幻般残留在老成都人的记忆里。惟有人民公园那家独一无二的茶铺,还使人依稀记起“绿荫阁”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