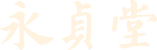历史地看,孟子“不动心”的意蕴主要是在道德修养论意义上被视为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即主体或人心以普遍的道德原则(义)经年累月地约束自身:一方面,内心能动地认知超越的理或普遍的道德原则(知);另一方面,心自觉地以自身所认识之理约束自身,不为外物或利欲所牵引而弃理滑离开去(行)。这一具有认知主义倾向的理解,显然将“不动心”的意蕴窄化了。本文从道德—生存论角度出发,强调“不动心”的意蕴必须在基于具体行事(道德实践活动)的整体性境域中来加以理解。①
一、心(志)在心气一体的整体中具有主体性
从《孟子》本文来看②,公孙丑追问的关键是:如果得卿相之位,可以大有作为(形式上实现道)而“王霸不异”,是否动心?
就孟子思想的主旨而言,心自身当然一开始就必然处在一种自我展开的动态之中:“心焉能不动?裁说不动,便是道家之‘嗒然若丧’,佛氏之‘离心意识参’,儒者无是也。”③心总是处于“动”之中,在此意义上依然说心不动是什么意思?换言之,心本就是“动”的,而这里所否定的“心动”,是什么意思?心本即在动,动作为行事当然与物关联。因此,此心动的意思,显然不是说心与物在行事中发生了关联,而是说在行事中心为异己的力量(卿相之位)所牵引而远离自身。公孙丑所谓“动心”,意味着在某一行事活动中,“心”将之前不行事时而认可的东西(王道仁政)抛弃,而拥抱了一种新的东西(现实的权位与利欲)。孟子回答说“不动心”,则是在行事活动中,心恒在其自身、持守于自身。
公孙丑不明白在行事活动的整体中心持守自身,而将孟子所谓不动心理解为一种武士式的“勇”,即以为孟子勇于坚持一种与现实政治割裂的、外在的理念。公孙丑之意,勇是孤零之心对于自身所选择对象的偏执坚持。但在孟子,勇是在心与气的关系上实现的:“‘养气’一章在不动心,不动心在勇,勇在气。”④“养勇即是养气。”⑤如此所谓勇,不是公孙丑意义下的勇,“未尝非勇,而不可以勇言。”⑥
在孟子对北宫黝、孟施舍到子夏再到曾子的渲染中,孟子首先否定了北宫黝、孟施舍那样专守其气而丢失其心的勇,然后以曾子否定了子夏博而无守。王夫之认为,曾子之“守义而约”并非“反求诸己”(单纯内指而制约内心):“曾子之言大勇,与孟子引此,则意在缩,而不在自反。缩者,集义也。唯其缩,乃能生浩然之气而塞两间。”⑦在王夫之看来,孟子所谓不动心之勇,是心在世界整体之中经由行事集义而使存在的道德性(浩然之气)充满此一世界整体。这里有两点需要强调:其一,此一世界整体之谓世界整体(王夫之所谓两间),是基于具体行事而有的统一整体;其二,这一基于具体行事而有的统一整体,以心气一体为其本体论基础。与孟子“不动心”将心置于此一整体世界而不动摇相比,由孟施舍乃至告子,则因割裂心与气裂为二而动易了心的本然样子:“施舍有气无志,告子无志无气,曾子、孟子以志帅气,则有志有气。”⑧不动心的根源是有心有气、心气一体,而心能在与气互动中持守自身而真正不动。简言之,不动心的首要意蕴是:心将自身的具体行动展开于与气一体的整体世界中。
从理论上说,道德生存的具体境遇包含着心物与群己两方面关系。在现实之中,两者并非截然相分,而是统一在一起的。具体现实的行动,展开为心、物(气)与他人(社会,这里主要以言为表征)三者的统一。告子之不动心,表现在言、心、气三者关系上,将三者彼此隔绝而固守不动:“告子谓于言有所不达,则当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于心;于心有所不安,则当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于气,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动之速也。孟子既诵其言而断之曰,彼谓不得于心而勿求诸气者,急于本而缓其末,犹之可也;谓不得于言而不求诸心,则既失于外,而遂遗其内,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仅可而有所未尽之辞耳。若论其极,则志固心之所之,而为气之将帅:然气亦人之所以充满于身,而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为至极,而气即次之。人固当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养其气。盖其内外本末,交相培养。此则孟子之心所以未尝必其不动,而自然不动之大略也。”⑨显然,朱熹强调了言、心、气三者的相通一体的关系,不能主观地对三者加以阻断孤守(其中心与志可以说一个东西,因为志是心之所之,亦即具有内容与指向的心即是志),在现实行程中,心(志)与气是一种动态的交养关系;并且,心气一体中,心为主、为本,气为次、为末。
心气在现实活动中的交养关系,基于心气的本然一体。对于心或志与气的本然一体,黄宗羲说:“天地之间只有一气充周,生人生物。人禀是气以生,心即是气之灵处,所谓知气在上也……心即气也……志即气之精明者是也,原是合一,岂可分如何是志,如何是气?”⑩但心气之本然一体,是在二者统一的现实活动中实现的,是一种动态的统一关系。王夫之从动态展开的角度,认为孟子此处志气关系分为三层,“第一层以志为主,而气从志令,曰‘帅’,曰‘至’,曰‘持其志’,所重在志。告子一定拿着个主意,不为物动,与此相近,故上曰勿求于气可也。然此自无志及志不正者言之耳,则以持志为重。第二层言志与气有互助为功之道……志气交相为功,志以作气,气亦兴志,两者俱不可不求,既以明‘勿求于气’之非果可矣。第三层就气之有功于心,全重在气上,则就能持其志者上说,此时全恃气以配之。”(11)在动态展开过程中,由于主体自身在过程的不同阶段上具体处境的差异,心、志与气的关系也有轻重缓急与层次之别。心气一体在动的意义上的一体,也就是下文所说的在具体行事中的一体。
综上而言,不动心作为心气一体基础心的主体性表现,即是心在自身展开的活动过程中而不偏离自身,它蕴涵着两方面的要义:一是心展开自身的活动本身处在与万物一体的整体性(本体论)境域之中,因此,心的自身展开就不是将心隔绝于外物而孤守自身;二是在万物一体的整体性境域中展开自身就是自觉于其主体性的实现。
告子与孟子不动心的差异,就在于告子是“强制不动”或“硬把定”,孟子则是“酬酢万变而不动”(12)。孟子自认为知言与养气作为超越告子之不动心的两个方面,就是在心气一体的动态整体中,心持守自身。
二、浩然之气是对心气本然一体的道德转化
如上所说,气是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的共同本体。气本来通天地而浑沦弥漫为一整体世界,这是自在的气一体相通的世界。作为人自身体之充的气,也就是弥漫天地之间的气:“天地吾身之气非二”;“气只是充乎体之气,元与天地相流通。”(13)从道德-生存论立场来看,自在的气一体相通,仅仅是一种承诺——除了承认它是道德实践行动的基础之外,不能赋予更多的内容,世界的一切内容来自道德之践履与修养。
在孟子,气之浩然的意思,当然不是指气的本然通为一体,而是这种气之本然通为一体在道德上的自觉,即达到自为的气之通为一体。所以朱熹说:“气,一气。浩然之气,义理之所发也。浩然之气是养得如此。”(14)“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气即所谓体之充者。本自浩然……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别。浩然之气,乃吾气也。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一为私意所蔽,则欿然而馁,却甚小也。’谢氏曰:‘浩然之气,须于心得其正时识取。’又曰:“浩然是无亏欠时。”(15)在朱熹看来,浩然之气即是心得其正而无所亏欠时人的整体性存在。
浩然之气需要“养”,就是“必有事焉”的行为,即“浩然”是通过主体自觉道德实践,渗透道德性主体力量的一气流通。王夫之说:“吾之气有浩然不易养也,而我必求善养焉,善养之,而后庶几其浩然也……吾身之气一有不振,则即吾身之欲为有不能行;然必不能坐而听气之自生,亦不能起而期气之必壮。吾求之,乃吾善养之;吾益求所以善养之,乃成乎其浩然。”(16)气之浩然首先依赖于作为主体的“吾”之求与行,即气因着主体的善养乃成其为浩然。王夫之强调,“善养而后庶几浩然”,“不能坐而听气之自生”,这里蕴涵着两层重要的意思:一方面,由主体的善养行为之展开,气由自在而自为,即浩然之气是经由主体善养行为而由自在之气转化而来;二是作为主体的人之善养其气,是通过能动行为养自身之气,并行而及于身外之气,从而身内身外之气一气浩然。善养力行并不必然成就气之浩然,但是,不善养、力行,则必然不能浩然。所谓浩然的意思,在此意义上,就是指人作为主体经由自身的道德实践活动,将道德的意味从自身之气充盈注入身外之气,使原本自在一体的内外之气由道德实践行为而贯通转化为道德性的浩然之气。气之浩然与否,不是气的自在状态,而是主体道德实践的产物。但回溯地看,气之所以能经由主体的能动道德实践而浩然,当然基于人一身之气与身外之气本自一体(或说“本自浩然”)。所以,内外本自一体的气,是合乎道义的道德行为展开的基础,此即所谓“配义与道”。
由于浩然之气是在主体性道德实践基础上的本然一体之气的道德化,因此,孟子说浩然之气“难言”。何以难言呢?王夫之解释说:“夫浩然之气,唯有诸己者自信其盛大流行之无可御,而言之则难也。盖言其藏诸己者之实,则不足以尽其用之大,而或近于硁硁之气节;言其加诸物者之盛,则不足以知其本之厚,而或近于一往之风裁;言其固有而不待于安排,则人皆具此气,而何以或全或丧;言其矜持而始成其大勇,则人可鼓其气,而即以无愧而无忧。”(同上,第190页)“难言”的意思是说,浩然之气是切实的修养行动之所得,是实有诸己的流溢,是一种道德生存论状态,不是理智的言说之所能切中。在言说中,追问何以能如此这般“浩然”,则不过说为“我本藏有”,但说我本藏有则不能将其多样而丰富的实际展开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从而流为一种无实行的气节;如果说浩然就是如此这般在诸多事物上表现出来的作用,则不能厘定其在主体自身内在的实有,流为一时的风格气象而已;如果单单说是每个人天然就有的,自然而然就会如此展现流淌出来,则无法说明何以有的人全此浩然有的人却丧失此浩然。因此,浩然不是一种语言相应的状态,相比于知言作为群己关系上的体现,浩然之气是个体性自身内在的德性修养,更多地依赖于个体在切己实行中的领悟与自证。
浩然之气作为自在一体之气的道德转化,它是心为主之气:“气,只是这个气。才存此心在,此气便塞乎天地之间”(17)。心为主于浩然之气中,就是主宰与道理的统一,“只是中有主,见得道理分明。”(同上,第1255页)心为主于气之中,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心以自身获得的理使气获得了道德性规定,也就是说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义是行之宜,它有两个方面,一是心的方面,一是气的方面。浩然之气是心与气一体的道德化,即心对与自身一体的气赋“义”而成。浩然之气作为道德一精神性的气,它至刚至大,反过来促进着心依循于道义而行。气的道德化与道德化的气之能合而有助于道义的实现,两者统一起来,就是浩然之气所表达的意蕴。但是,二者的统一,作为集义活动,实现于具体行事之中。
三、集义以养气奠基于具体行事之中
从道德生存论看,“必有事焉”其实是理解整个“不动心”章的枢纽,它是集义而生浩然之气的基础。“必有事焉”意味着主体性活动的源初性,或者说,心一开始就自觉自身展开在具体行事之中。“必有事焉”阐明了事情或行动的本质,就是心在一个整体性世界中实现自身。就文本展开来说,“必有事焉”是用以解释如何“集义”的,而不是直接回答“养气”(浩然之气以集义而生)。
集义以生浩然之气,其基础是“必有事焉而勿止”。“必有事焉”,即人必然处于行事之中,而行事必有其“义”。行是内外之气交互影响、相互作用,因此,行事之义(宜),当然内在于此交织的气中,因此,“气与道义,只是一滚发出来”。(同上,第1245页)就气与心在动态中的一体而言,告子与孟子不动心的区别在于活与死之别:“孟子是活底不动心,告子是死底不动心。”(同上,第1261页)活当然是心的本质所在,它无时不在“活”的展开中,也就是心在具体行事中集义而不移异。如上所说,心总是处在动之中,实质上也就是人总是处在行事之中:“人于日用之间,无时无地之非事,即无时无地之非动。”(18)行事活动具有根源性,行事之宜(义)先行展现于行事活动之中。《朱子语类》有一个记载:
问:“《集注》云:‘告子外义,盖外之而不求,非欲求之于外也’。”曰:“告子直是将义屏除去,只就心上理会。”因说:“陆子静云:‘读书讲求义理,正是告子义外工夫。’某以为不然。如陆子静不读书,不求义理,只静坐澄心,却似告子外义。”(19)
朱陆在心与理上的分歧暂不论,就集义而养浩然之气来说,朱熹强调读书求理的行事活动,通过具体行事活动而集义,这更为接近孟子的本意。因此,以行事为基础是理解集义的核心,“集义是行底工夫”(同上,第1261页),“‘必有事焉’,是须把做事做。”(同上,第1264页)经由行事而集义,在一定意义上是因为人并不能对义生而知之:“若集义者,自非生知,须是一一见得合义而行。若是本初清明,自然行之无非是义,此舜‘由仁义行’者。其他须用学知。凡事有义,有不义,便于义行之。今日行一义,明日行一义,积累既久,行之事事合义,然后浩然之气自然而生。”(同上,第1263页)在行事中认知义,积累义,才能最终自然而生浩然之气。通过比喻,孟子既反对“舍而不耘”又反对“拔苗助长”,要突出的是气浩然一体的根基在于“必有事焉”,即心无时不在行事之中展现自身。而行事有两种异化自身的表现方式,即“舍而不耘”与“拔苗助长”——前者“不”行事而后者以“私意”行事。
由行事而集义,其实质在于必须将心与义理解为内在于同一行事活动之中。所谓义之内在,在此意义上,是事之宜,有其自在性;而事本身是人作为主体的行动,因此,心具有对于事之宜的宰制与掌握,有其自为性。而就心物在本质上同在“行事”之中而言,义作为事之宜,作为行事之原则或规范,它是心物二者在行事之中共存的法则,不能认为行事之原则或规范单纯来自心,或单纯来自物。因此,义是“心之制”与“事之宜”在具体行事中的统一。无论以义单纯归为心之产物还是归为物之属性,都是“义外”之说。如上文所举,朱熹与陆九渊互相指斥对方为告子义外之说,其原因就在于二者都没有真正理解孟子所谓“必有事焉”的意思,就是集义只能在具体行事中实现,义从行事中经由心的明觉而逐渐彰显。简言之,义与事不能分离,义是心在力行行事之中、从事情中所集:“‘集义’者,应事接物,无非心体之流行。心不可见,见之于事,行无所事,则即事即义也。心之集于事者,是乃集于义也。”(20)因此,行事活动本身具有优先性,“义”是心作为主体性力量展开行事之所“集”。
事之宜内在于事情,事情按其本质而展开,“义”就能到来。如果悖于事情自身的展开而人为任意地介入或离弃事情,都是事之不“宜”。“必有事焉而勿止”(21),人“活着”就是“行事”,就是事情永不停止地依据自身本质而展开、延展。在此行事过程中,“心勿忘”,即是说心必须一直内在于事情之展开过程,并主宰这一过程;而“勿助长”则是要根据事情本身的展开而得其宜(义),不能脱离了事情任自身理智妄为,反过来外在地介入事情而使事情失其宜。(22)孟子将“不耘者”与“揠苗者”视为两种脱离行事具体性的表现,认为两者都失其宜,而不能集义而生浩然之气。不耘者是忘却种植之事(失却了“必有事焉”的源初情态),揠苗者是不顾庄稼自身的法则而主观助长。在具体行事中得宜而集义,只要勿忘、勿助长即可:“‘勿忘、勿助长’之间,正当处也。”(23)所谓“正当处”,即是行事之宜所在。既然义是行事之宜,而行事本身又是不断展开的,因此,义也是随着行动而不断生成的:“义,日生者也。日生,则一事之义,止了一事之用;必须积集,而后所行之无非义。”(24)
义作为事之宜,本质上随着事情的变化而变化,不过,一旦它为心的认知能力所把握,又能获得相对的独立性,取得相对于实际行事的外在客观性而体现为单纯为心所颁布的性质。但从根源上看,义的相对独立性是逐渐生成的。
四、知言是在社会性存在中明理分辨而自觉担当人之类本质
知言关涉的是道德存在中的群己关系,它是不动心的另一个环节或方面,即个体存在的合群性或其存在的关系性(即必然与他人同处共在)方面。虽然从一般意义来看,“知言”是对不同观念的评断。但是,恰如其分地评断世间不同的纷纷言说,不仅仅是因为评断者有一个不可遮蔽的清明之心或者心把握了唯一天理。实质上,知言关涉到语言的本质问题。从语言的本质来看,言语自身构成着评判言语的更为坚实的基础。某种或某些言论之扭曲乃至陷入诐、淫、邪、遁,当然首先应该是从言语自身的本质给出的断定。语言是人存在的关系性或合群性表现,知言也就意味着在存在的整体性中与他人之关系在“言说”上的合理性确定。就此而言,对于人的存在,语言具有本质性。一方面,语言植根于人类的共同行动并使共同行动在更高的阶段上展开。在共同行动中,既要将行动的共同对象加以确定,又要将所有行动主体的个人理解加以传递。人类群体的整体性活动构成着语言的前提,“社会群体是语言的条件”。(25)
如果说养气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抽象为基于个体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心与气的关系)而言道德实践(修养行为),知言却只能在群体或社会整体活动中才能得到确定。虽则孟子乃至后世的诠释并未能明确而充分给出“社会性”作为理解知言的基础,但是,言说的社会性本质无疑构成我们进一步理解孟子知言的基础。正如恩格斯所说,语言是在共同劳动中基于合作劳动的必须而产生的,社会性或者合群性共同活动是理解语言的基础。由此,语言的表达必然关涉着言说者与倾听者两方面。就道德意义而言,商谈伦理学(或说对话伦理学)认为,道德原则必须基于主体间的理性对话与交往而建立,强调真正的道德个体只有在社会化过程中才能形成,即有见于此(26)。
如果语言基于群体生活,个体只有在群体生活中才能获得自身,那么,一切言说对于社会性主体都具有内在性。朱熹说:“言之所发,便是道理。人只是将做言看,做外面看。且如而今对人说话,人说许多,自家对他,便是自家己事,如何说是外面事!”(27)言之所发,总是对话,其间自有“道理”。告子以言为外,所以不得于言则不求于心,其实,与于言说者或对话者,言说或对话并不在自身之外。自己即是能动的参与者,自己即是此对话、言说的内在参与者,必回返其心而获得主体性。
正因为言发生于合群生活之中,因此,孟子的知言,其指向就不是自知而独善其身。心所知之理,发于口则为言,发于身则为行。一定意义上,就政治—道德生存而言,政事的展开,就是心—理的实现。在乱世(乃至任何时代),政治治理者并不必然掌握着合理施政的理论,而往往为邪说诬言所惑。知言就是对邪诬之言的本质的明了,知之则当辨明之,防止其为害于政事。王夫之说:“吾既知之矣,则守吾之正而听彼之自起自灭于天下,不亦可乎?而固不可也。言不自言,而终以喊道诬人,坏人心而终不可兴王业者,皆在于此。”(28)因此,孟子知言就不是离弃天下而孤守一心,而是明正道于天下而待王者,斥邪说而使之不害天下——无论世道如何卑污,心守此而不动。
与“知言”相联系,孟子“好辩”即知言以论世。为什么“必须(非得)”知言而又好辩于世?因为,人当然而必然地处身存活于“人群”之中,即孔子所谓“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论语·微子》)。知言而好辩,显现为社会责任的担当,其实质是社会责任担当与维护个体存在之家园的统一(在此意义上,个体的存在之善与群体生存处境的善是统一的)。孟子的不动心,则是在社会整体中知言而辩其是非得失,知言辞之诐、淫、邪、遁而明其蔽、陷、离、穷,并以道义匡护此世。所以,孟子说“圣王复起必从吾言”。而告子的不动心,是遗弃天下事务而孤守一心,王夫之以之为类似于佛道异端逃世避世之行。
因此,知言的不动心意蕴在于:个体生存于社会整体之中,虽然由之而获得自身存在的可能,但是,个体却不随着社会整体的堕落扭曲而移异自身,而敢于担当矫正社会扭曲的责任。在孟子,知言与好辩统一,是孟子自觉的使命、责任承担,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批驳导致人心淆乱的邪说诬言;二是将传承历史中维系人自身本质存在的事业。前一方面体现为由“好辩”而做论定:“杨朱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所谓无父无君,就是对人存在的社会整体性的背弃。而对无父无君的禽兽论断,不外乎是要以突出的方式强调人不能脱离人自身的整体而存在。在孟子看来,政治治理的恶,就来自于治理者自身从与民一体的整体性存在中倒退滑落。无论在对梁惠王与民同乐的论说中,还是对诛一夫纣也的辩解中(29),都可以看到孟子对治理者与民一体的强调。
知言而好辩的另一方面,则是孟子自觉地接续了从禹到周公再到孔子的事业:“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认为禹之所做,是将洪水以及龙蛇等导入河道,使人能在大地获得居所;周公则在大地成为家园之后,将非人的猛兽和夷狄驱逐出去,使大地真正成为人的居所;孔子则是在统一的社会整体作为居所分崩离析之际,对人群整体最能彰显人性的那些社会治理者作出《春秋》笔法(将背离了人之整体居所的乱臣贼子加以揭露并提示属人的政治理想);孟子则是对战乱时代影响君王们的观念学说加以剖别,拒斥那些导向非人生存可能的言说,而在无圣的时代,存留下“将来”圣王复起而必从之言。简言之,孟子认为自己承继三圣人,在不断变化的具体历史境域中,从事于维系人之为人本质的事业。
由此,知言作为不动心的一个方面,其意蕴是在社会性整体存在中,勇于担当对类本质的维护。
五、“学孔子”的意蕴在于经由整体而成就自身
在“不动心”章的最后,孟子讨论了孔子与伯夷、伊尹的同异,更论及了自己与孔子以及孔门诸弟子的关系,其结论则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从义理上看,学孔子意味着孟子通过知言养气以论不动心之后的自我认同,其中蕴涵着他在道德生存论上的价值取向,也是其所谓不动心的最终意蕴所在。要明白孟子学孔子的意蕴,就要明白他所说“孔子贤于尧舜”、“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自有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以及“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等等,究竟何所指?王夫之解释说:“圣人之于民,亦同此形,则同此义、同此知,亦类也,而圣人者,为民所不敢为,不为民之所竞为;于其同类之中,高自标举以伸其志,而超然自拔于流俗萃聚之中……则孔子之贤于尧舜者何也?为百王之不逮者何也?为出类拔萃之圣人所莫及者何也?道义统其同,而仁智立其异,吾之所愿学者此矣。”(30)人之为人,当然不是在生物-物理意义(即形的意义)上的界定,而是在一定自觉行动中贞定的。所谓一般民众,就是其行为不能区别于他人而与他人混同为俗,在流俗中,似乎都是“人”存在于其中,但究实而言,无任何真正自主的人活于其中。圣人不在流俗中,因为他凭借其切实的具体行为与一般民众区分开来。圣人与民同类为人,但圣人不与民同俗而为,他走出了流俗萃聚之类而成其为自身。孟子原文本来说孔子对于民众而言“出类拔萃”,王夫之进而理解为即使是出类拔萃的圣人也不及孔子,将孟子学孔子的意蕴更为彻底地彰显出来。圣人走出了“流俗萃聚之类”,而圣人不再成为一个“类”。
在通常的理解中,似乎有一些人间的精英,他们天赋过人,自身构成着一个超越一般人类的“圣类”。在孟子的本意以及王夫之的理解中,不存在这样一个圣人之“类”,圣人的本义就是在自己身上完全实现自身者,它拒绝抽象的类别划分,而是切于行动的自身实现者。因此,尧超乎一般人流俗萃聚之类而成就为尧之自身,舜超越于一般流俗萃聚之类而成就为舜自身,孔子也超越于流俗萃聚之类而成就为孔子之自身。如上文所述,道义在即事集义过程中,慢慢取得相对的独立性,乃至获得公共普遍性,所以道义表达的是圣人与一般人以及所有圣人之同。但是,仁智却是个体在具体处境中的切己行事本身,不能被普遍化公共化。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孟子·离娄上》)仁作为安宅、义作为正道,其真实的内容就是事亲从兄的具体活动,而智对于事亲从兄活动的意义,就是使之抵达于“自觉而持守”(知之而不离开)。当智仅仅限于对事亲从兄之行事的自觉时,仁义就没有被脱离行事而被智抽象地加以孤立化,行事活动本身就是个体化的。
由此,孟子所以要学孔子者,恰好是不能被学的东西。那么,孟子说学孔子究竟学什么呢?王夫之说:“‘愿学孔子’一语,乃通章要领,若于前后贯通有碍,则不但文义双踬,而圣学吃紧处也终湮晦,令学者无入手处。夫愿学孔子,则必有以学之矣。孟子曰‘可以仕则仕云云孔子也’,然则将于此而学之耶?乃此四者则何易学也?仕、止、久、速之可者,初无定可,而孔子之‘则仕’、‘则止’、‘则久’、‘则速’也,自其义精仁熟,由诚达几,有几入神之妙……孔子曰‘下学而上达’,达者自然顺序之通也。达不可学,而学乃以达,孔子且然,而况学孔子者乎?”(31)孟子所要学孔子者,即是这“下学”本身,也就是切己行事而明觉之。舜的形象和孔子的形象在《孟子》中表征着某种重要意象,对尧何以禅让于舜这一重大事件,孟子以“行事”为答,亦即舜经由自己的切己行事彰显自身而得禅让。
由此,孟子将自己与孔子的学生相比,并将孔子与别的历史圣人相比,其用意就在于:将知言的与群一体(与他人共在)指向自身志向与身份的确认,即“学孔子”。在与物一体中行事而习得主体性自觉(类的自觉),在与人一体中则获得真正的自身(个体性的自觉)——圣人的意思,就是在行事中切中自身。孔子的“仕止久速”,即行事之“时中”。时中的意思,就是在具体性的境域中抵达行为主体之自身。主体性自觉抵达一般的人,学孔子则抵达每个人的自身。以孔子为表征,孟子所要说的不是一个抽象意义的孔子之作为圣人是绝对的标准,而是说,孔子超出于所有人之外而成其为孔子,昭示着所有人成其为自身的道路。孔子既代表着人主体性的自觉,也代表着人自身个体性的自觉。
综上所说,不动心的意蕴,就是经由自身的切己行动、具体行事,在心物关系与群己关系上,处身整体之中而自为持守。换句话说,即主体经由自身的切己行动,通过成就自身为一个真正的人而为所有人之所以为人进行担当(既是使本然一气的世界成为“人”的世界,也是使相与为群的这个群体成为“人”的群体)。这才是不动心的完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