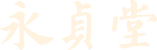一、引言
自郭店与上博的出土文献问世以来,先秦时期中国学术思想的研究几乎成为海内外的“显学”。考古学、文字学、历史文献学、学术思想史、哲学史等不同学科交织互动,正在逐渐改变并完善着我们对于先秦学术思想图式的既往认识。郭店竹简公布不久,杜维明教授即指出:“整个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史都需要重写。”①郭店与上博文献的出土导致先秦中国学术思想的重写,大概不会有人质疑,但是否会足以影响到整个中国学术思想史,则是问题。不过,如果这句似乎略显夸张的话意在强调不能仅仅局限于先秦时期的学术思想,而要根据出土文献新的思想内涵和意义来观照不同历史阶段之间学术思想的整体关联,那么,其间则确有深意存焉。尽管上博简还有部分内容有待整理出版,已经整理出版的郭店与上博文献在某些文字编连、训诂等方面也还不无异见,但哲学研究者已经可以根据确定的文献材料来进行“第二序”的诠释工作。②学界也的确出现了一些根据郭店与上博文献从哲学角度研究先秦思想的成果。然而,是否利用了新出文献将不同历史阶段的思想内容联系起来加以研究,或者更为明确地说,是否运用了新出文献从哲学角度来检讨不同历史阶段某些思想观念之间的内在关联,则是目前几近阙如的。
郭店与上博新出文献中以儒家的思想材料最为丰富,但围绕郭店与上博儒家文献进行的探讨,迄今为止海内外学界的成果恐怕都还没有越出先秦儒学的疆域。事实上,作为以前学者不曾见到的地下原始材料,郭店与上博的相关儒家文献不仅能够使我们更为全面、深入地重新理解先秦儒学,还可以为我们揭示和把握先秦儒学和宋明理学在某些重要思想观念之间的连续性与连贯性,提供坚强的依据。没有郭店和上博的这些相关文献,那些思想观念在内涵上的连续与一贯性,我们是无从观察和论证的。就儒学的哲学思想层面而言,先秦儒学与宋明理学或许是传统儒学中最为重要的两个阶段。但现代的研究者尤其专治先秦儒学的学者,往往要么忽略二者之间的关联,要么过于强调二者之间的差异,认为后者由于吸收融会佛老的缘故而不免远离了前者的精神。这当然有时是对宋明理学缺乏深入了解所致。而个别较为注重二者连续与一贯性的学者,在论证其间的连续与一贯时尽管可以说理推论,却又常常因缺乏直接的文献根据而失之笼统,难以服人。本文将以郭店和上博的相关儒家文献为据,详细指出并论证在“性”、“情”和“无”这三个具体的重要观念上宋明理学与先秦儒学之间的连贯性。
二、性
宋明理学对于人性问题的理论,往往是通过对于先秦儒家尤其是孔孟人性论的诠释而提出的。但是,宋明理学家的诠释是他们自己的创造性发挥,还是能够符合先秦儒家人性论的致思取向而有“调适上遂”的展开,以往是难以衡定的。因为对于先秦儒家人性论,我们以前基本上只能了解孟子与荀子之说。尽管我们对于孟子和荀子论“性”的不同层面与理论基础可以有较为明确的分疏,从而认识到双方先验论与经验论的视角不仅未必冲突,而且能够互补。但是,从孔子语焉不详的“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一句话,如何而有孟子的“性善”论?其间蕴涵怎样的端绪和脉络以及应有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如何在整个先秦儒学的全局中观照那些不同人性论之间彼此的理论关联,从而把握其应有的展开,我们缺乏足够的文献依据来加以探讨和论证。如今,随着郭店竹简《性自命出》以及上博竹简《性情论》等儒家文献的问世,我们不仅得以对先秦儒家人性论的丰富内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同时也获得了考察宋明理学人性论与先秦儒家人性论彼此关联的基础。
在整个宋明理学的传统中,不同学者对于人之“性”的理解自然有所差异,但作为大部分学者基本接受的“大端”,关于“气质之性”与“天命之性”(或“天地之性”、“义理之性”)的理论,则是宋明理学传统在人性论方面最具特色的理论贡献。其中,张载(1020—1077)、程颐(1033—1107)发其端,而以朱熹(1130—1200)的总结最为周密。
周敦颐(1017—1073)已经既认可人们自然气质的多种表现是人之“性”,所谓“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③同时又认为“诚”是人的本性,纯粹至善,源于宇宙的乾健本性。但周敦颐的这一思想表述得极为简略,张载则明确提出了“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的对比。所谓“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也”④。前者是指人的自然气秉或性格,包括“刚柔”、“缓急”、“才与不才”等,后者是指天地原初的道德属性以及人的本性。“气质”虽然也可以称之为人的“性”,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所在,却不在于前者而在于后者。因此张载说“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也”。对于“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二者之间的关系,张载没有过多的讨论。程颐则进一步关联于先秦儒家的人性论指出,孟子的“性善”之“性”,作为“极本穷源之性”,是人最根本的“性”,告子所谓的“生之谓性”说的是“气质之性”,是指人受生之后的“性”。告子意义上的“性”尽管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但也不能说不是人之“性”。对于先天的善性与后天的气质,必须同时兼顾,如此方是对人性的全面理解,所谓“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⑤这种看法,程颐更是用来诠释孔子和孟子对于人性的不同表述。对于如何看待孔子的“性相近”与孟子的“性善”,程颐认为,孔子所谓“性相近”,讲的“只是气质之性,如俗言性急性缓之类。性安有缓急?此言性者,生之谓性也。”“生之谓性”不过是“论其所禀也”,而孟子“言人性善”,则是论“性之本也”。⑥
作为程颐思想的继承者,朱熹对于这样一种诠释的思路十分欣赏,他认为张载、程颐“气质之性”之说“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而朱熹对于“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论述,与其“理”、“气”关系的看法相配合,在理论上更趋严密。大体来说,朱熹认为人性禀受天地之理而来,人未生之前,天地之理流行于天地之间,在禀受到一定形气之后,才构成现实的人性。但是,“理”一旦与“气”相结合,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污染。因此,现实的人性已经不是性之本体了。而“理”与“气”融合所构成的现实人性,即“气质之性”。在这个意义上,“气质之性”可以说是超越的性善之性与经验层面的感性欲求的混合。所谓“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⑦对此,朱熹曾有一个很生动的灯笼之喻,所谓“且如此灯,乃本性也,未有不光明也。气质不同,便如灯笼用厚纸糊,灯便不甚明;用薄纸糊,灯便明似纸厚者;用纱糊,其灯又明矣;撤去笼则灯之全体著见。”⑧这就是说,“天命之性”就好比灯笼的光明本身,“气质之性”则如糊上厚纸、薄纸以及纱之后灯笼透出的光明。现实中每个人所表现的人性正如蒙有各种灯罩的灯笼透射出来的光,已经不是未经灯罩的灯光本身了。当然,这种看法与张载有关“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关系的看法尤其对“气质之性”的理解似乎稍有不同,⑨但是,注意到“性”同时具有超越的层面和感性经验的层面这一点,可以说是包括朱熹和张载在内几乎整个宋明理学人性论的基本共识。
总之,宋明理学传统对于“性”的主流看法是兼顾到“人之所以为人”的先验的本善之性和人们种种气质差别所造成的后天的有善有恶之性。作为“天命之性”,前者可以说是超越层面普遍的共同人性;作为“气质之性”,后者则可以说是经验层面分殊的差别人性。当然,正如朱熹对于“理”“气”关系的看法一样,所谓“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只是逻辑分析的方便说法,在实然的层面上,这两种人性则是合在一起的。正如程颢所说,“故不是善与恶在性中为两物相对,各自出来”。⑩这种看法,无论较之孟子的性善论还是荀子的性恶论,以及孟、荀以后汉唐各种人性论,如性三品说和性善恶混说,显然在理论解释力上更为周延与融贯。但是,这是否完全只是理论发展的一种“进化”,是宋明理学家的“创造”,还是在先秦古典儒学中渊源有自呢?
事实上,孔子之后对于人性的看法后来之所以有孟子先验性善论与荀子经验性恶论的两端发展,并不是偶然的。而在孟子之前的儒学中,对于人性的理解已经蕴涵了兼顾人性的“共相”与“殊相”或者说“一”与“多”这两个不同层面的端绪。这一点,在郭店竹简《性自命出》篇中有明确的反映。上博简《性情论》也是一篇讨论“性”、“情”的文献,且与《性自命出》颇多重复之处。二者相较,《性自命出》篇的内容较为完整。因此,对于新出土儒家文献中“性”、“情”问题的讨论,本文将主要以《性自命出》为据。
目前关于《性自命出》篇中的人性论思想,专治先秦思想的学者大都认为其中“性”的诸多表述颇多矛盾冲突或至少是不一致之处。细检《性自命出》中所有关于“性”的语句,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性”的不同理解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如其生之自然之质”言性,亦即从感性经验的层面来理解人性,譬如:
喜怒哀悲之气,性也。
好恶,性也。另一类,则是从超越层面的根源角度以及人之为人的共同本质来理解人性,譬如:
性自命出,命自天降。
四海之内,其性一也。
未教而民恒,性善者也。上引这几段文字,可以说是最能反映这两种对“性”的不同理解的代表性文献。如果我们侧重根据第一类的两段话来看“性”,自然会认为《性自命出》的人性论是从人的自然气质来规定人性,接近荀子一系。而如果理解“性”的主要根据是第二类的三段话,那么,我们很容易得出《性自命出》的人性论与《中庸》孟子性善论如出一辙的结论。就此而言,从孔子关于人性善恶的语焉不详到孟子的性善论再到荀子的性恶论,其间并非突兀而缺乏必要的逻辑环节。正是由于孟子之前《性自命出》篇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中已经同时蕴涵着先验性善论与经验性恶论的两种端绪,后来有孟子和荀子各自沿着这两种不同端绪的进一步分化和展开,就是很自然的了。
进一步而言,如果我们不囿于先秦儒学的言说脉络,充分考虑以上所论的宋明理学中关于“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分疏,那么,我们显然会发现,第一类对于性的理解正是从“气质”而言性,而第二类则无疑说的是“天命之性”或“义理之性”。在这个意义上,从《性自命出》篇中的人性论分化出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的两端,最后在宋明理学的话语系统由“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这一对观念得到妥帖与周延的理论安顿,可谓是“理有固然,势所必至”的。
如此看来,尽管《性自命出》篇中对于人性的讨论远未像后来理学传统中对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及其关系的说明那样细致和精巧,但却未必是自身内在的矛盾和冲突,反倒恰好可以说既是孟子和荀子性善论与性恶论两极分化的近因,更是宋明理学传统中“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观念得以充分展开的远源。前者治先秦思想的学者多已有所发明,后者由于以往未能将宋明理学与先秦儒学关联起来考察,则似未有学者论及。
三、情
除了“性”之外,对于先秦儒学与宋明理学之间的连贯与连续,《性自命出》篇中的“情”这一观念同样具有极为重要的启示意义。迄今为止,学界普遍认为,《性自命出》中“情”观念的出现,修正了以往仅以先秦文献中“情”为“情实”的看法。(11)当然,这一点的确可以说是《性自命出》一文中“情”字的重要意义。不过,除此之外,《性自命出》中“情”观念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同样在于显示了宋明理学与先秦儒学在思想观念上的一脉相承。
无论在中西方的哲学传统中,至少中古以来,“情”一般被理解为感性经验层面的“情感”和“情绪”,道德情感也不例外。但是,“情”是否只能是一种感性经验层面的东西,是否可以有一种具有本体地位和超越性的“情”,在儒家传统中却一直存在着肯定的看法。譬如,对于孟子的“四端之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以及“辞让之心”,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就认为,作为一种道德情感,孟子的四端之心并不只是一种感性经验层面之“情”,而是具有超越性,可以称之为一种“本体论的觉情”(ontologicalfeeling)。(12)这种“情”的特点就是既具有先验本体的地位,同时又会落实、表现或作用在感性经验的层面。在批评康德有关道德情感的问题时,牟宗三就引孟子四端之心为例,来说明这种同时贯穿“体”与“用”或者说先验与经验的道德情感。(13)牟宗三这种对于儒家传统尤其孟子作为四端之心的“情”的理解,后来在其学生李明辉那里得到了更为细致和周密的分析与论证。(14)唐君毅也曾经指出,这样一种具有超越性和本体论地位的先天的道德情感可以称之为“天情”。(15)对此,许多学者往往认为,这是现代儒家学者引入西方哲学以为诠释和比较的结果。事实上,笔者这里要指出的恰恰是,这种对于“情”的理解在宋明理学传统中其来有自,并非只是引入西方哲学话语的结果。并且,宋明儒者对于“情”的这种理解,也同样不是“凿空自创”,而是在《性自命出》中已经有所滥觞。
在宋明理学的传统中,“情”基本上被理解为“性”的已发状态。或者说,“性”与“情”之间具有一种“体用”的关系。这种看法更早可以追溯到唐代李翱(字习之,772—841)《复性说》中所论述的性情论。在“性体情用”的思维模式下,“性”一般被视为超越的“未发”,而“情”则被看作已经落在经验层面的“已发”。但是,既然“性”是超越的存在,那么,作为“性”的直接发动的“情”,是否可以不必一定下落到感性经验的层面而同样具有超越性的意义层面呢?事实上,在宋明理学的传统中,已经有学者提出了这种意义上的“情”的观念。
王畿(字汝中,号龙溪,1498—1583)曾经提出过“至情”的观念,他在《答王敬所》第二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夫意者,心之用;情者,性之倪;识者,知之辨。心本粹然,意则有善有恶;性本寂然,情则有真有伪;知本浑然,识则有区有别。苟得其本,盎然出之,到处逢源,无所待于外。意根于心,是为诚意;情归于性,是为至情;识变为知,是为默识。(16)在这段话中,作为“根于心”的“诚意”、“归于性”的“至情”以及“变为知”的“默识”,显然都不同于一般有善恶夹杂的经验意识和感性情感。
王畿这种“至情”的观念并非其独唱,就连对王畿颇有微辞的刘宗周(字起东,号念台,学者称蕺山先生,1578—1645)也有类似的观念。以往儒家传统一般都将“喜怒哀乐”视为“形而下者”,也就是属于感性经验的层面,但刘宗周却明确将《中庸》里面的“喜怒哀乐”之“情”与一般所谓“喜、怒、哀、惧、爱、恶、欲”这“七情”区别开来。在刘宗周看来,“喜、怒、哀、惧、爱、恶、欲”这“七情”是感性经验层面的情感与情绪,而《中庸》的“喜怒哀乐”之“情”,则是和“心”、“性”、“理”一样是居于“形而上”的层面的。譬如,他在《学言中》中就曾经这样说过:
《中庸》言喜怒哀乐,专以四德言,非以七情言也。喜,仁之德也;怒,义之德也;乐,礼之德也;哀,智之德也。而其所谓中,即信之德也。(17)并且,除了“仁、义、礼、智”之外,刘宗周还将“喜怒哀乐”与孟子的“恻隐、羞恶、是非、辞让”这四端之心相配。他说:
恻隐,心动貌,即性之生机,故属喜,非哀伤也。辞让,心秩貌,即性之长机,故属乐,非严肃也。羞恶,心克貌,即性之收机,故属怒,非奋发也。是非,心湛貌,即性之藏机,故属哀,非分辨也。(18)刘宗周特意将“喜怒哀乐”称之为“四德”或“四气”,(19)目的就是要将这种“情”与一般的“七情”区别开来。在他看来,后者是感性经验层面的情感和情绪,前者则是心性的直接表现。心性本体所具有的超越性,同样是“四德”之“情”的内容规定。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王畿的“至情”还是刘宗周的“四德”之“情”,作为一种心性本体直接发动的道德情感,显然不能是理性感性严格二分意义下的单纯感性的道德情感。牟宗三、唐君毅和李明辉等现代新儒家对于孟子四端之心的诠释,无疑在宋明理学中有其根据,完全可以和王畿“至情”以及刘宗周“四德”之“情”的观念先后呼应。事实上,即便在西方,也并非完全没有类似这种对于“情”的看法。(20)
再进一步,本文所要强调的是,宋明儒家的这种超越性的“情”在先秦儒学中也是有所根据的。如今新出土的儒家文献可以让我们看到,在先秦儒家那里除了具有“情感”的意义之外,“情”还不仅仅指一般意义上感性经验层面的情感和情绪,同时也有类似王畿、刘宗周以及后来现代新儒家学者所诠释的那种超越性的“情”。这一点,作为《性自命出》等新出土儒家文献的意义所在,是以往的研究者未有措意的。
正如“性”一样,作为《性自命出》中出现频率极高的一个观念,(21)“情”也同样包含两个不同的意义层面。首先,和通常的理解一样,“情”是指感性经验层面的自然情感和情绪。譬如,“凡至乐必悲,哭亦悲,皆至其情也”以及“用情之至者,哀乐为甚”这两句话里面的“情”字,所指都是人的感性经验层面的自然情感和情绪。
但是,除了这一意义层面之外,“情”字还有其超越性或“形而上”的意义。譬如,《性自命出》中关于“情”还有这样两句话:
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
未言而信,有美情者也。未教而民恒,性善者也。在第一句话中,既然和“性”、“命”、“天”、“道”以及“性”处于同一序列,那么,“情”就很难只是感性经验层面的具体的“喜怒哀乐”等情感和情绪,而应当具有超越的“形而上”的意义。作为“性”的直接所“生”,作为“道”之“始”,这里的“情”应当是具有超越性同时又最为内在的人性的最初显现。在第二句话中,关于后半段“未教而民恒,性善者也”中“性”的涵义,我们前文已经指出。如果前半段话“未言而信,有美情者也”与后半段话“未教而民恒,性善者也”具有并列的关系,那么,这里具有“未言而信”特征的“美情”,也应当和“人之所以为人”的本善之“性”一样,是具有超越性或“形而上”意义的人之所以为人的本善之“情”。并且,如果“美情”的特征是“不言而信”,而“信”即“信实”之意,那么,这种以“信”、“实”为其内容的“情”,可以说非常接近《中庸》文本中具有内在超越性和本体地位的“诚”这一观念。
事实上,《论语·子路》中有这样一句话:
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22)其中,和“情”相对应的也是“信”。而对于这里的“情”字,朱熹在《论语集注》里的解释也正是“诚”,所谓“情,诚实也。”
这样看来,正如现代新儒家对于“情”的诠释可以在宋明理学中找到其合法性的依据一样,宋明理学传统中如上述王畿、刘宗周从超越层面来理解的“情”,在先秦儒学中也可以说是有其“源头活水”。从《性自命出》篇中的“情”到王畿的“至情”、刘宗周的“四德之情”再到牟宗三的“本体论的觉情”,其间的连续与一贯同样清晰可见。
四、无
就“性”与“情”这两个观念来说,虽然以往的研究者在利用郭店和上博新出土的儒家文献时未能将先秦儒学与宋明理学关联起来加以考察,但是,无论在新出土文献的文本语境中还是在先秦儒学的领域中,对这两个观念本身还是进行了穷深研几的考察,这也构成笔者本文思考的基础。不过,对于“无”这个观念,情况则有所不同。上博简中《民之父母》篇中记载孔子有“三无”之说,迄今的研究非但没有将其关联于宋明理学,即使在先秦儒学的疆域中,讨论似亦远不及“性”和“情”充分,大都仅限于其论述的政治意涵本身,顶多由之意识到“无”在先秦已经并非道家思想的专利,并未由此思考儒家意义上“无”的哲学蕴涵。(23)事实上,如果能够关联于宋明理学的传统,我们可以看到,上博《民之父母》篇中“无”的观念意义相当深远,它可以充分说明宋明理学家所阐发的“无”的观念未必源于佛教和道家,而是在孔子那里有其直接的渊源。并且,儒家从孔子“三无”到后来宋明理学传统尤其阳明学者所阐发的“无”的观念,具有自身特定的理论内涵,与佛教本体论意义上的“无”根本不同。在这个意义上,宋明理学中尤其阳明学者“无”的观念,完全可以说是儒学传统的故物,只不过在佛教的刺激下得以充分彰显而已。
在宋明理学中,对于“无”的观念阐发最为有力的是阳明学的传统。从嘉靖六年丁亥(1527)天泉证道开始,在中晚明围绕“无善无恶”的不断讨论辩难中,儒家“无”观念的丰富内涵得以展开。王阳明(1472—1529)晚年已经用“无善无恶”来形容道德本体,(24)王畿在天泉证道时提出“四无”论,对于王阳明四句教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中“无”的意蕴做了进一步的发挥。而在万历二十年(1592)的“九谛”、“九解”之辩中,周汝登(字继元,号海门,1547—1629)更是不仅对阳明学所理解的“无”的涵义进行了全面的澄清和解释,同时还追溯了这种“无”的涵义在儒家思想发展历史上的一贯性和谱系,试图为这种“无”的合法性提供历史的论证。
关于阳明学中“无”的涵义,有研究者曾进行过详细的分疏。(25)大体来说,阳明学以“无善无恶”来形容良知或心性本体包括两层涵义:一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至善;一是境界论意义上的无执不滞、自然而然。前者是本质内容,后者是作用形式。对此,当时阳明门下不乏相应的了解。如何廷仁(字性之,号善山,1486—1551)曾说:“师称无善无恶者,指心之应感无迹,过而不留,天然至善之体也。”(26)董澐(字复宗,号萝石,晚号从吾道人,1457—1533)也曾说:“性者,天地万物之一原,即理是也。初本无名,皆人自呼之。以其自然,故曰天;脉络分明,故曰理;人所享受,故曰性。生天生地,为人为物,皆此而已。至虚至灵,无声无臭,非惟无恶,即善字亦不容言。然其无善无恶处,正其善之所在也,即所谓未发之中也。”(27)之所以选择“无善无恶”来表示至善,是由于一般日常语言中的善,都是指与恶相对的经验层面的善。而作为道德本体的心性与良知,则是绝对的至善或者说善本身。这种绝对的至善或善本身与经验层面善恶相对的善是不在同一层面的。这是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来看道德本体。因此,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无善无恶的说法只是为了不使对作为道德本体的至善的理解落入相对的善恶之中的善,并非如佛教“空”、“无”观念所表示的那样否认世间万事万物的终极实在性,所谓“本来无一物”(通行本《坛经》)、“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龙树《中论》),而是指人生境界论意义上的一种精神气质和存在状态。
从境界论的意义上来看,道德本体的“现身情态”(存在状态)与流行发用又具有无执不滞、自然而然的先验品格。这种在落实于经验层面“为善去恶”、“是是非非”的情况下又不自居于“善”、自居于“是”的品格,也是“无善无恶”一语所要揭示的道德本体的境界论向度。在工夫论的意义上“无善无恶”的“无”则是指我们在进行为善去恶的道德实践时不要执着于自己所为的“善”,如此才能使良知心体自然呈现并起到主宰的作用。从这一角度来看,切实把握到良知心体这种不着是非善恶的境界论向度,甚至是保证道德实践真实性的必要条件。所谓“无善即进善之捷径,无非乃去非之要津”(28)。只有在消解了心灵执着与造作的情况下,作为最真实存在的良知心体才能朗然呈现出来,真正的道德实践如孟子所谓“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才得以可能。如此看来,那种在落实于经验层面“为善去恶”、“是是非非”的情况下又不自居于“善”、自居于“是”的“无”的品格,反映的正是道德本体境界论而非本体论的向度。这种境界论意义上的“无”不必是佛道两家的专利,而毋宁可以说是儒释道三家的共法。
在回应许孚远(字孟中,又作孟仲,号敬庵,1535—1604)“九谛”的“谛九”时,周汝登在其“九解”的“解九”中有这样一段话:
若夫四无之说,岂是凿空自创?究其渊源,实千圣所相传者:太上之无怀,《易》之何思何虑,舜之无为,禹之无事,文王之不识不知,孔子之无意无我、无可无不可,子思之不见不动、无声无臭,孟子之不学不虑,周子之无静无动,程子之无情无心,尽皆此旨,无有二义。天泉所证,虽阳明氏且为祖述,而况可以龙溪氏当之也?(29)这里,周汝登追溯儒家“无”的思想谱系,其实也恰恰是要论证这一观念在儒家思想史上的连续与一贯。在他看来,王畿的“四无”说并非其“凿空自创”,甚至作为王畿四无论直接思想根据的王阳明四句教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也不过是“祖述”而已。因此,这种“无”,实在可以说是儒家传统的一贯之道。周汝登此处根据儒家经典的记载而枚举历史上儒家代表人物所标示的那种“无”的境界,甚至追溯到孔子之前的舜、禹和文王,可谓言之有据。而如今,上博简中新出土的儒家文献《民之父母》中孔子所谓“三无”的记载,可以说为海门的论证提供了直接有力的文献支持。
上博简中《民之父母》中关于孔子“三无”之说的记载是这样的:
子夏曰:“五至既闻之矣,敢问何谓三无?”孔子曰:“三无乎,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君子以此横于天下。系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也;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也。而志气塞于四海矣。此之谓三无。”(30)孔子这里所说的“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并不是要取消“乐”的“声”、“礼”的“体”和“丧”的“服”本身,而是要使“乐”、“礼”和“丧”在实践过程中达到“无声”、“无体”和“无服”的效果。这种效果,就是“乐”、“礼”和“丧”完全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内发行为,而不是刻意要去符合的外在规范。因此,“无声”并不是不要通过“声”来实现“乐”,而是说“声”的表达自然而然,不觉其有“声”;“无体”并不是不要通过“体”来实现“礼”,而是说“体”的表现自然而然,不觉其有“体”;“无服”也并不是不要通过“服”来行“丧”礼,而是说“丧”礼的行使自然而然,不觉其有“服”。所谓“系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也;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也”,正是用来形容“乐”、“礼”和“丧”那种自然自发的效果和境界。
如果说“无”只是“乐”、“礼”和“丧”的作用形式,那么,除了这种作用形式之外,“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还有其内容规定,并非空无内容。孔子紧接着“三无”之后的“五起”之论,就是对“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的本质内容的说明:
子夏曰:“三无既得而闻之矣,敢问何诗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无声之乐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无体之礼也;‘凡民有丧,匍匐救之’,无服之丧也。”子夏曰:“言尽于此而已乎?”孔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之服,犹有五起焉。无声之乐,气志不违;无体之礼,威仪迟迟;无服之丧,内恕孔悲。无声之乐,气志既得;无体之礼,威仪翼翼;无服之丧,施于四国。无声之乐,气志既从;无体之礼,上下和同;无服之丧,以畜万邦。无声之乐,塞于四方;无体之礼,日就月将;无服之丧,纯德孔明。无声之乐,施及子孙;无体之礼,塞于四海;无服之丧,为民父母。”这里,“无声之乐”的本质内容是“不违”、“既得”、“既从”的“气志”,有如此的“气志”为内容,“乐”就可以“塞于四方”、“施及子孙”。“无体之礼”的本质内容是“迟迟”、“翼翼”的“威仪”,(31)有如此的“威仪”为内容,“礼”就可以“上下和同”、“日就月将”并“施及四海”。“无服之丧”的本质内容是基于“纯德孔明”的“内恕孔悲”,有如此的“恕”和“悲”,就可以“施于四国”、“以畜万邦”从而“为民父母”。事实上,在《孔子家语·六本》和《说苑·修文》中,这种具有“无”的作用形式的“乐”、“礼”和“丧”的本质内容恰恰被明确界定为“欢”、“敬”和“忧”。所谓“无体之礼,敬也;无服之丧,忧也;无声之乐,欢也。”
显然,“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中的“三无”和阳明学“无善无恶”中的“无”具有表述形式上的一致性。正如“无善无恶”并不是在本体论上的意义上否定“善”的终极实在性,而是认为只有在“不居其善”的“无”的状态之下,真正的“至善”才能得到体现,所谓“无善之善,是为至善”。同样,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乐”、“礼”和“丧”,“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可以说也就是“至乐”、“至礼”和“至丧”。并且,只有达到“无声”、“无体”和“无服”的境界,“至乐”、“至礼”和“至丧”才能真正实现。事实上,《大戴礼记·主言》中有一段类似的话:
孔子曰:至礼不让,而天下治;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至乐无声,而天下之民和。这里,“至礼”的“不让”、“至赏”的“不费”以及“至乐”的“无声”,可以说和《民之父母》中的“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是基本上对应的。(32)这也为我们以“至乐”、“至礼”和“至丧”来诠释“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提供了支持和佐证。
《民之父母》中的孔子“三无”之说,其实并不是首次见于世。以往的传世文献中已经有与之几乎完全一样的表述。在《礼记·孔子闲居》中有这样一段话: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闻之矣,敢问何谓三无?”孔子曰:“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君子以此横于天下)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也;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也;志气塞乎天地。此之谓三无。”而关于“三无”本质内容的“五起”之说,《礼记·孔子闲居》中也有几乎和上引《民之父母》中孔子论“五起”的表述完全一致的说法。只是第四段论“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中的“塞于四方”变成“日闻四方”。最后第五段论“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变成“无声之乐,气志既定;无体之礼,施及四海;无服之丧,施及孙子。”语句有变,但文意无别。
除了《礼记·孔子闲居》之外,上述《民之父母》中“三无”、“五起”的表述也曾经出现于《孔子家语·论礼》中,但由于《孔子家语》历来被认为是王肃伪作,以致《礼记》中的孔子言论以往学者多不敢引以为据。像论“三无”这样的话,则历来被认为是道家思想,从未引起深究。如此一来,即便《论语·卫灵公》中明确有一处透露孔子“无”的思想的话,所谓“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也为后来几乎绝大多数学者语焉不详地忽略过去了。如今上博简《民之父母》的出土证明孔子“三无”说的真实不虚,则既可以打消现代学者的疑虑,更足以证明宋明儒家学者的许多论证在先秦儒学中有其思想的根据了。周汝登认为王阳明和王畿所阐发的境界论意义上的“无”并非“凿空自创”,在儒家传统中“究其渊源,实千圣所相传者”,也可以说获得了“二重证据”的支持。
当然,在境界论的意义上而言,宋明理学中“无”的观念受到佛教尤其禅宗的巨大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认为这种“无”的观念儒家传统中本来没有而完全是来自于佛道两家。《民之父母》中“三无”说的意义,恰恰可以为“无”这个观念从先秦儒学到宋明理学之间的连续与一贯提供进一步的文献依据。
五、结语
宋明理学构成先秦儒学的发展,这可以说是学界的常识。但是,对于“发展”的涵义,其实一直存在一个基本的理解,即宋明理学是吸收了佛道两家尤其佛教许多思想因素的结果。如本文所论“性”、“情”和“无”三个观念,以往大都认为是佛教影响下的产物。因此,就宋明理学对于先秦儒学而言,所谓“发展”的真正涵义,在不少学者的心目中,其实可以说是“断裂”大于“连续”、“歧异”大于“一贯”的。认为宋明理学偏离了先秦儒学精神方向、两个阶段“所同不胜其异”者,亦所在多有。佛教对于宋明理学形成和发展的刺激之大和影响之深,笔者和诸多学者一样有充分的自觉和了解。但同时,笔者在研究过程中也日益认识到,宋明理学中许多以往认为是来自于佛教的观念,其实是先秦儒学的故物,只是在佛教的刺激下在宋明理学中获得了更为明确和周延的表达而已。借用佛教的说法,佛教的刺激和影响只是“缘”,而先秦儒学中固有的观念则是“因”。以上,本文根据郭店和上博的相关新出土文献,通过对“性”、“情”和“无”三个观念的考察可见,至少在一些重要的思想观念上,先秦儒学与宋明理学之间更多的是“连续”和“一贯”,而非“断裂”和“歧异”,两个阶段可以彼此发明,并非肝胆楚越。本文以宋明理学与先秦儒学之间的连贯为题,正在于强调这一点。既希望对以往关于先秦儒学和宋明理学关系的“常见”略尽补偏救正之力,同时,也意在显示如郭店和上博竹简等新出土文献的意义并不限于先秦思想研究的范围。在笔者看来,20世纪一系列新出土的文献不仅可以修正和丰富我们对于年代久远的先秦时期思想世界的认识,如果善加运用,还可以藉之以观察不同思想阶段之间的关联,开拓出新的视域。
除了可以让我们看到儒学思想史不同阶段之间的连续和一贯之外,郭店和上博新出土文献中的一些观念,譬如本文讨论的“情”和“无”的观念,还可以有助于破除以往一些思维定式。那些思维定式其实经不起稍许推敲,但人多习焉不察。其中常见的一个就是对先秦不同思潮尤其儒道两家持一种“区隔化”(compartmentalization)的理解。所谓“区隔化”,就是认为两家思想不能有交集或任何的“重叠共识”。这实际上是将儒道两家双方思想的丰富性加以化约和彼此隔离,然后再用这种抽象和化约后的“何为儒”与“何为道”的标准去进退原始文献,合者不必言,不合者即使显然为儒家文献,也必判之为“伪托”、“窜入”。实在无法剔除,也会在对后来的儒学传统并无深入了解的情况下断言为“后儒”所忽略。显然,借用王夫之(1619—1692)的话来说,这种思维方式是典型的“立理以限事”。而事实上,很多观念在不同的思想传统比如儒释道中往往是共享的,只不过轻重有所不同而已。如果不能够根据原始文献来不断修正自己的既有观念框架,“即事以穷理”,而是始终固守一些化约和抽象所获致的“标准”,从而对各种思想系统进行本质主义的简单理解,所谓“立理以限事”,对任何思想系统恐怕都是难以登堂入室的。
目前,治古典儒学(汉以前)者往往于后来的宋明理学置之不顾,更不论现代新儒学了。当然,从学术分工的角度而言,整个儒学史的各个阶段都需要各自的专家学者,治先秦者可以不必兼长宋明,反之亦然。但是,这只能视为学术分工或者研究者时间精力的自然限制,如果将宋明理学和现代儒学对古典儒学的诠释一概视为“污染”和“扭曲”,无视宋明和现代儒者对古典儒学的任何理解,则未免偏见与无知了。由于宋明理学基本上是一个经典诠释的传统,即通过对古典儒家经典的不断诠释来建构自己的思想系统,因此,宋明儒者对于儒家古典的娴熟程度和理解深度,就决不是今人在缺乏了解的情况下所可以妄议的。如今治古典儒学者如果不能对宋明儒者的古典诠释有充分的了解,其所得有时也就难以渡越以往宋明儒者相关的古典诠释,惟不自知耳。学术总是由积累而不断发展,后来者要想真正于作为儒学源头活水的古典儒学有所创发,以往儒学历史上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可轻忽。就儒家哲学传统而言,眼下治古典儒学不仅不能绕过宋明新儒学,现代新儒学也同样是不能回避的。否则的话,势必自小门户而难免株守之限。打个比方,处在黄河或长江的入海口,要想了解其源头之水,必须要溯河或溯江而上,随江河的蜿蜒而尽其曲折,在充分了解江河水之来龙去脉的基础上,对于源头的点滴之水的丰富内涵,方能有充分的了解。否则,黄河与长江的源头,对观察者来说,恐怕不过是与朝露和雨滴无分轩轾的点滴之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