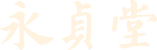《四库全书总目》云:“况之著书,主于明周孔之教,崇礼而劝学……至其以性为恶,以善为伪,诚未免于理未融,然卿恐人恃性善之说,任自然而废学,因言性不可恃,当勉力于先王之教。故其言曰:凡性者,天之所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四库全书总目》,第770页)这段话当然有很强的针对宋儒的味道,并有回护荀子的意思,但总的说来,还是持平之论。“明周孔之教,崇礼而劝学”的概括,阐明了荀子之学的大体;如果再加上“化性而起伪”这五个字,就是对荀学精确而全面的理解。荀子作为战国末期的儒家巨匠,活跃在百家争鸣的思想氛围之中,其学问必须在丰富的诸子学背景里才能获得了解。而尤其重要的,则是儒家内部丰富的传统。如果从《荀子》书里来看,儒家内部的子思和孟子构成了荀子不可或缺的对话者。这种对话直接地表现在《非十二子篇》和《性恶篇》等篇。荀子的很多主张,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看作是对思孟的反动,如以性恶对抗孟子的性善,已经为学者所熟知。本文想以《劝学篇》为主,从学与思的角度,对荀子与思孟的差别进行另一角度的理解。
一、学的主题
《劝学篇》位居《荀子》三十二篇之首。此种编排始自刘向,为后来治《荀子》诸家所沿袭。其中有无深意,值得探讨。古代文献中,大凡居首者,多被赋予特殊之意义。如《诗》之《关雎》,《易》之乾坤,《老子》之首章,《庄子》之《逍遥游》,在后世的解释者看来都有标明宗旨或突出主题的作用。儒家文献中,《论语》的编纂结构和《荀子》颇有类似之处。《论语》始于《学而》,终于《尧曰》;《荀子》始于《劝学篇》,终于《尧问篇》。这种相似也许不是出自偶然:如果相信《论语》的编定是在《荀子》之前的话,那么就该是《荀子》的编纂者在形式上刻意模仿前者。二者共同形式背后体现的则是类似的义理结构,即“由学以致圣”的思想路径。此路径在《论语》中已见端倪,到了荀子表达得更加显豁。如果从此角度来考虑的话,那么《劝学篇》之被安置在《荀子》之首,就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包含着一个整体的思想上的考虑。这个考虑的核心乃是对“学”本身的重视,而其隐含的问题比这要复杂得多。我们如果把它放在儒家思想内部“判教”的角度上来考虑,《劝学篇》其实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具体来说,它针对的是思孟学派过分强调“思”的倾向,以及与此相关的对于性与心等的不同理解。由此阅读的话,《劝学篇》在《荀子》以及儒家思想史中的意义就重要得多。
从内容上来看,《劝学篇》当然是一个全面的关于“学”的讨论。随着该篇的展开,我们会逐渐了解,荀子论述“学”的角度,主要的不是和知识相关,而是和德性与生命密不可分。在荀子看来,学习的过程就是生命不断塑造和提升的过程,或者一个道德生命成就的过程。与“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类似,“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如果把“知明”理解为道德知识,“行无过”理解为道德践履的能力,那么可以说,这种知识和能力并非生而具有,而是必须通过“学”的方式才能实现。荀子认为,人是很容易受外界环境影响的存在:“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接受什么样的教育,或者从事何种内容的学习,对一个人来说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这句话看起来似乎是对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说法的直接解释;无论如何,荀子和孔子都共同强调后天努力尤其是学习对于生命而言的重要价值。正是后天的学习与否以及学习的内容,决定了一个人生命成长的方向。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荀子把学习理解为一个“积”的过程:“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此种积,如“积善成德”所指示的,主要的仍然不是知识的积累,而是德性的蓄积。
这种对学的理解也就规定了学的范围。按照荀子的说法,学习的对象主要是经典所代表的先王之遗言:
不学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劝学篇》)
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也。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同上)
在这里,学被从两个层次上进行了描述。一个是数的层次,即学习的具体科目和次序:从诵经开始,到读礼结束。从这里的叙述方式和后文来看,所谓诵经中的经,主要该是指《诗》《书》而言。从孔子开始,《诗经》和《尚书》就是儒家最注重的经典。“终乎读礼”,既是指阅读和学习的次序,又体现着荀子一再强调的隆礼的旨趣。此种顺序,与孔子所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有表面的相似之处,但在实质的精神上却有很大的差别。另一个是义的层次,即学习的宗旨和方向:从为士开始,到为圣人结束。根据这种理解,学习主要的是和人格生命的培养和完成有关。结合荀子他处的说法,士、君子、圣人是他关于人格生命几个阶段的基本区分。学习的终极目的是成为圣人,这乃是一种“全之尽之”的状态。荀子在该篇的篇末也称之为“成人”:
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也。(同上)
这里的成人,其实就是大成之人的简称。如孟子所说“孔子谓之集大成”,乃是人格生命完成了的状态。因此目的,学习就不是为人的口耳之学,而是为己的身心之学:
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同上)
君子之学和小人之学的区别就在于:后者的学问仅仅表现在口耳,是一种外在的装饰;前者则是关乎整个生命之事,通过真积力久而入心的工夫,德性可以在整个的生命中呈现出来。也因此,学习最切近的办法是“近其人”。它涉及的不是简单的文字或者知识或者死的东西,而是对活生生的生命的体认。通过一个理想的生命形象,例如古代的圣王或者圣人,来感受理想的生命人格,从而找到一条最方便的路径。拘泥于过去的经典是无用的:“《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故曰:学莫便乎近其人。”(《劝学篇》)文字化的经典是死的僵化的,表现的只是过去的经验;只有把它们和生命联系在一起,才会有普遍的价值。
荀子的为学,除了近其人之外,最重要的是“隆礼”:“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隆礼次之”。(同上)在荀子看来,这关乎整个学问的宗旨。隆礼才能知其统类,得其经纬。不如此,即便终日读书,仍是一无所得。基于此,荀子对于仅仅知道“顺《诗》《书》”的“陋儒”表达了不满:
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礼,安特将学杂志,顺《诗》《书》而已耳,则末世穷年,不免为陋儒而已!将原先王,本仁义,则礼正其经纬、蹊径也。……不道礼宪,以《诗》《书》为之,譬之犹以指测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锥餐壶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礼,虽未明,法士也;不隆礼,虽察辩,散儒也。(同上)
荀子的学术,可以说是外辟诸子,内正儒门。但以《劝学篇》而言,明白针对的主要是儒门内部。“儒分为八”,虽然荀子没有明白地指出他所谓的“散儒”或者“陋儒”何指,但稍作分析就不难发现,这里针对的主要是子思和孟子一系。一方面,思、孟对《诗》《书》的注重是毋庸置疑的,《五行》全篇只引用《诗经》,和子思关系密切的《中庸》也是如此。(参见王博)《孟子》之作,司马迁认为是“序《诗》《书》,述仲尼之意”(《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结果,衡之于全书,这个说法是合理的。另一方面,他们从《诗》《书》中引出的主要是注重内省的心性之学,而不是荀子所看重的礼学,因此荀子才批评思孟是“不道礼宪”的散儒。
《劝学篇》包含着几个对于了解荀子以及儒家思想来说相当要紧的观念,这里集中地澄清一下。首先,荀子对于学的理解,并不仅仅是着眼于教育或者修身的角度,而是把它视为涉及生命本质的问题。从“学不可以已”,到“学至乎没而后止也”,这些说法都表明学该是和生命相始终的。对于道德生命而言,学是其得以成就的前提。所以,学可以看作是荀学的中心观念,并和其他一系列的观念有着内在的联系。其次,对学的强调,从逻辑上来说包含着一个重要的前提,即人是非自足的或者有缺陷的存在,所以需要通过后天的工夫来塑造和弥补。至于这种缺陷是什么,以及到什么程度,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在荀子那里,当然是其性恶的主张。性恶代表着人的生命中存在着根本上的缺陷,因此需要转化。而在化恶为善的过程中,学就构成了重要的枢纽。再次,生命的缺陷决定了生命主体需要借助于他者来改进和完善自己,单纯依赖生命内部的发掘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学习的过程被荀子描述为“善假于物”的过程。“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应该有明确的针对性,这就是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的主张。最后,如果说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会导向反身的内省,即所谓的“思”,那么荀子则对于“思”表现出了明显的怀疑和否定:“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如果把这句话放在和孟子的对话中,其意义就变得异常的明晰。
二、思的工夫
如上所述,荀子《劝学篇》的论述乃是有为之言,明显地针对着子思和孟子一系的主张。这里尤其要强调的是学与思之间的相对和紧张的关系。孔子就曾经在相对的意义上讨论过学与思,最著名的说法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在《论语》中,孔子一方面强调“好学”,另一方面也突出“近思”,似乎表现着一种学思并重的态度。但是,从子思开始,“思”得到了压倒性的强调。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近几十年来陆续发现的帛书和竹简的《五行》篇,学者们一致认为它们是子思或者子思学派的作品。帛书的《五行》有经有说,竹简《五行》只有相当于经的部分内容。该篇的主要内容是强调仁义礼知圣五行与心的连接;它从“形于内”和“不形于内”出发,发展出一套独特的天道和人道学说。在这个学说中,“思”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先来看看如下的一些说法:
思不精不察,思不长不得,思不轻不形。不形则不安,不安则不乐,不乐则无德。(《五行》)
在一系列的双否定句法中体现出来的逻辑是:思不能达到某种状态则无德。不难看出,思被看作是有德的逻辑前提。这里所谓“德”,如果结合《五行》篇的论述来看,指的是仁义礼知等“形于内”的状态:
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义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礼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知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同上)
此处的“内”,其实就是心的代名词。因此,所谓的“形于内”指的是落实或者扎根到内心之中。德的状态是指仁义礼知等并不仅仅是口头或者表面的东西,而是完全根据着内心的要求。唯有如此,此种德行活动的实践才会伴随着安与乐的感觉。同时,德也被描述为天道,以与作为善的人道相区分。①德与善、天道与人道的区别就在于那些德目有没有心灵的根基,《五行》云:
君子无中心之忧则无中心之智,无中心之智则无中心之悦,无中心之悦则不安,不安则不乐,不乐则无德;君子无中心之忧则无中心之圣,无中心之圣则无中心之悦,无中心之悦则不安,不安则不乐,不乐则无德。
可以看出,德的前提乃是中心之忧,以及由此而来的中心之智和中心之圣。正是由于这种理解,和中心有关的“思”作为达到“德”的工夫才被正式提了出来。通过某些形式的“思”,“形”(“形于内”的简称)才成为可能,换言之,仁义礼智等才会被内在化,成为和心不可分割之物。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是,子思学派是如何理解思的呢?首先可以肯定,这是一种与心有关的活动。其次,由于“心无定志”,这种与心有关的活动需要在方向上加以规定。孔子所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就是要给心之思规定一个方向。而在《五行》中,这个方向由无邪被明确化为仁义礼知圣。不难看出,“形于内”的过程不仅仅是仁义礼知等在内心的扎根过程,同时也是给内心规定方向的过程。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五行》为什么对思进行了具体的规定。思被要求着从“精”、“长”和“轻”的方向展开。什么是思之精、思之长和思之轻呢?《五行》继续说:
不仁,思不能精;不智,思不能长;不圣,思不能轻……仁之思也精,精则察,察则安,安则温,温则悦,悦则戚,戚则亲,亲则爱,爱则玉色,玉色则形,形而仁;知之思也长,长则得,得则不忘,不忘则明,明则见贤人,见贤人则玉色,玉色则形,形则知;圣之思也轻,轻则形,形则不志,不忘则聪,聪则闻君子道,闻君子道则玉音,玉音则形,形则圣。所谓思之精乃是对仁的思,由精而察,经过了安、温、悦、戚、亲、爱等,达到玉色的状态;至此,仁才算是最终落实到了心上,并表现在整个的生命中。色在《论语》中就常被提起,孔子说的君子九思中,就包含“色思温”(《论语·季氏》)一项。从《五行》来看,玉色显然是经过了内在心灵润泽之后的形体之颜色。它的获得是在一系列的精微之思的基础之上,从安到爱所表现的都是内在心灵很细腻的情感变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仁之思才被称为精。相应地,思之长和思之轻则分别对应着知和圣。所谓的长应该是指思向外部的延伸,譬如贤人的发现。轻则是思的上升之旅,伴随着对君子道的把握。读者可以发现,《五行》关于思的分疏十分细腻,这在之前的文献中是从来未见的。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分疏首先针对的是内心的世界,而不是外部的物理世界。孔子曾经说过:“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他所提供的工夫主要是在生活世界的人伦实践中展开的。而在这里,求仁而仁至的工夫则表现为有节奏、合秩序的心之思。对于知之思和圣之思,我们也可以作出同样的理解。不难发现,在子思这里,思被看作是德行内在化的必由之路。正是通过思,仁义礼知等才和心建立起了内在的联系,从而进一步呈现在人的整个生活世界之中。
与重视思的工夫相适应,作为能思主体的心在《五行》中被明白地确立为生命的主体:“耳目鼻口手足六者,心之役也。心曰唯,莫敢不唯;诺,莫敢不诺;进,莫敢不进;后,莫敢不后;深,莫敢不深;浅,莫敢不浅。”如果把生命分为心和耳目等两部分的话,那么心无疑该是处于主导地位的,耳目鼻口等的活动必须由心来安排。对此,战国中期以后的《孟子》、《庄子》、《管子》、《荀子》等都有类似的理解。但是若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几乎是类似主张的最早者。事实上,如果考虑到《五行》中的“形于内”即是指扎根于内心的话,那么心的概念就该是《五行》思想的核心。
子思和孟子是否可以构成所谓的“思孟学派”,还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但是在对思的重视上,孟子确实是受到了子思的重要影响,并给予了进一步的发挥。思被明确看作是心的重要功能,因此有“心之官则思”(《孟子·告子上》)的提法。以思为标准,孟子把生命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能思的心,他也称之为大体;另一部分是不能思的耳目等器官,他称之为小体。思的意义在于生命通过它才可以把自身与他者区别开来,并理解自身的存在本质,从而确认自身的独立性与主体性。耳目之官不思,因此耳目是没有“自己”的;逻辑地推下来,也就没有自我和他者区分的自觉。当耳目和外物接触之时,就会因无法区分自身和外物而被外物蒙蔽和牵引。但是心不同,通过其思的能力,心可以确认自己在生命和世界之中的独立存在,并且确认自己内在地固有某些东西,正是这些内在固有的东西构成了生命的根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已。”(同上)如果说在《五行》中,仁义礼智等只是通过思实现了和心的连接,那么,孟子则大大地进了一步:在思中,心意识到仁义礼智乃是自身固有之物。它们是天赋予的,和后天的努力无关,因此也不可能通过后天的工夫嵌入到内心中去。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孟子论述心其实有两个层次,一个是良心或者本心,它的内容就是作为仁义礼智之端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或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另一个则是作为能思主体的心。对孟子来说,这当然不能说是两个心,它们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正是通过能思的心,良心或者本心才可以呈现出来,不至于淹没在物的世界中。孟子引了孔子的话说:“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向。其心之谓与?”(同上)操舍决定了存亡,这当然不是在本心有无的意义上来说的,它所突出的该是良心的呈现与否和操舍有着直接的关系。从孟子的立场看来,操就是思,舍则是对思的放弃。因此,学问的目的就是通过此思的工夫,来保持和扩充此先天的良心。“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同上)而所求的方式,也舍思莫属。如果离开了思,则心的放是必然之事。孟子论天爵与人爵道:
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孟子·告子上》)
天爵是内在于自己者,人爵则是求在外者。两者的本末轻重只有在思中才能被理解,孟子继续说:
欲贵者,人之所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言饱乎仁义也。(《孟子·告子上》)
如所谓的“贵”、“人爵”,乃是他人给予的,他人当然也就可以剥夺。在这个领域,生命永远不能显示自身的主体性。这个结论只有通过思才能完成,因此思的结果就是确立以仁义为核心内容的道德生命对于人而言的根本价值。不思的话,就无法了解比“欲贵”更重要的德。
如果我们深入到孟子的思想之中就会发现,思已经不局限于工夫的领域,它直接的就是人的本质的一部分,也就是人道的一部分。“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这就是一个很清楚的表达。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把天道的内容规定为诚,显然是开辟了不同于传统的以天象来言说天道的新视域,从而把孟子的学派与道家等区分了开来。这个新视域的本质是把天道和人心进行一个内在的连接。诚不是别的,它首先是某种最真实无妄的状态,其次是最真实无妄的存在。因此,诚是合天人的。如果说通过天象来表示和规定的天道还需要借助于推的方式——推天道以明人事——连接到生活世界的话,那么以诚为内容的天道不需要任何的媒介就可以直接地落实到人的生命中。诚不是别的,就是根源于人心深处的状态和存在。在这种理解中,天和人通为一体。因此,思诚既可以说是对天道之思,又可以说是对人性中最真实的存在之思;逻辑地说,就是对作为生命本质的仁义礼智等的思。在思中,人发现了“仁义礼智根于心”的事实,这种思的结果就是确认了“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确认了人作为道德生命存在的优先性。
如果说《五行》之思实现了仁义礼智等德目和心的连接以及心与天的连接,孟子的思则通过引入性的观念,把这些德目与心、性、天都贯通了起来。在这种贯通之下,实践仁义礼智不再是人为的要求,而是内心的要求、人性的要求、天的要求。因此,道德行为同时就是事天和乐天的行为。孟子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保证道德生命的成立。这种结论不是通过学的方式从外部世界能够获得的,而只能是内向反省的结果。事实上,这是思的逻辑结论。思并不满意于仅仅是无邪的,或者把仁义等和内心联系起来;它必定要求仁义等就是心的本质,是所谓的“本心”,并且这个本心同时就是性与天道。唯有如此,思才算是暂时达到了它的终点。
三、学思之辨
荀子和子思、孟子虽然同属于儒家,但他们在学派内部的对立却是显而易见的。在《非十二子篇》等中,荀子对子思和孟子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这种批评集中在诸如五行说和性善论等论题上。由于有帛书和竹简《五行》的发现,我们知道《非十二子篇》中所说“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也就是子思有关仁义礼知圣的理论;不过荀子批评的并不是这些德目本身,而是子思对这些德目与人心及人性之间关系的理解。子思和孟子一直在强调它们和心以及性之间的联系②,因此对五行和性善的批评其实是二而一的。由此出发,对于思孟特别注重“思”,荀子就提出劝学来对抗。最直接的说法见于《劝学篇》如下的一段话: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尤其是第一句话,其中思和学对比且对立的意味是非常清楚的。终日而思不如须臾之所学,也给这两种工夫定了高下。值得注意的是后面一连串的比喻,其实都和思与学有关。在荀子看来,学习的本质是借助于自我以外的事物来扩展、延伸或者提升自己,如同登高而招、顺风而呼,虽然手臂和声音并没有改变,但可以达到见者远闻者彰的效果;假舆马或者舟楫,虽非利足非能水,却可以致千里绝江河。这都是善假于物的结果。思却只是局限于自我的内部,如同翘足而望之所得,终不能与登高之博见相提并论。在荀子看来,自我之外有一个广大的世界,此世界不是通过闭门之思可以了解的:
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劝学篇》)
必须是通过学习,外在世界的博大以及自我的局限和缺陷才可以呈现出来,被我们自己意识到。同样也是通过学习,自我才可以得到提升,此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同上)。因此,外向的见闻就变得非常重要,它是通向外部世界的桥梁。荀子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如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不闻不见,则虽当,非仁也”。(《儒效篇》)纯粹的思是无意义的,《解蔽篇》中有如下一段话:
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觙。其为人也,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则败其思;蚊虻之声闻,则挫其精。是以辟耳目之欲,而远蚊虻之声,闲居静思则通。思仁若是,可谓微乎?孟子恶败而出妻,可谓能自强矣,未及思也;有子恶卧而焠掌,可谓能自忍矣,未及好也。辟耳目之欲,远蚊虻之声,可谓危矣,未可谓微也。夫微者,至人也。至人也,何忍!何强!何危!故浊明外景,清明内景,圣人纵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强!何忍!何危!故仁者之行道也,无为也;圣人之行道也,无强也。仁者之思也恭,圣者之思也乐。此治心之道也。
这段话同样有着很强的针对性。空石中人的名字觙或者就影射着子思(孔伋)③,这是个好思的人,因为担心与外物接触而影响他的思,所以就弃绝耳目之欲和蚊虻之声,在闲居静思的时候似乎能够达到通的状态。可是什么叫做通呢?通该是心灵和整个世界的相通④,而不仅仅是内心的自通,这种自通不过是不真实的幻觉。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不能回避和外物接触的,闲居的时候可以通(空石之人似乎有这样的寓意),那么和外界接触的时候呢?因此荀子反问道:“思仁若是,可谓微乎?”前面只讲到思,这里就出现了思仁。我怀疑它是直接针对子思而说的,《五行》中曾经提到“仁之思也精”的话,精不就是微的意思吗?但在荀子看来,这样的依赖弃绝外物的方式来思仁的做法,恐怕是不能够称为精的。与其说是精,还不如说是危!诸如孟子因为恶败而出妻,有子由于恶卧就焠掌,这也许可以称为自强、自忍,虽然难能可贵,但都属于此类。以荀子的看法,至人是无所谓忍、强和危的。圣人并非靠远离情欲的方式来控制情欲,如孟子所说的“养心莫善于寡欲”;他会直面情欲,但以理来进行节制。这里有的只是心灵实现大清明状态之后的从容,“兼陈万物而中悬衡焉”,如孔子所述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状态,而不是勉强、苦行和脆弱。“故仁者之行道也,无为也;圣人之行道也,无强也。”没有刻意的造作,也没有外力的勉强。如果真有思的话,那么这种思也该是到达某个阶梯之后的一种心情,如“仁者之思也恭,圣者之思也乐”⑤,而不再是一种主要的德行内在化的工夫。
至此,我们可以明确地了解,思孟与荀子确实是主张着两种非常不同的路径。前者看重的是思,而后者重视学。如果从成圣的角度来考虑,孟子主张“人皆可以为尧舜”和荀子说“涂之人皆可以为禹”是类似的,都在肯定普通的人能够成为圣人。但是其成圣的基础和工夫却截然不同。对孟子来说,其基础是每个人都有的善性或者良心,其工夫则是“反身而诚”的思。对荀子来说,其基础却是人性的恶,以及通过后天学习而能够掌握的化性而起伪的能力。我们可以把这两种工夫分别概括为思以致圣和学以致圣,它们代表着儒家内部的学思两途。思以致圣肯定生命内部的善性以及良心:道德的根源不能从外部去寻找,必须返回到生命的内部,因此把反身的思看作是确立道德生命的根本途径;学以致圣则相反:人性是恶的,没有所谓的本心或者良心,生命需要借助于外在的力量才能确立其道德的一面,因此需要通过学,通过虚一而静的心来了解作为生命之衡的道,进而由此道来规范自己的自然生命。可以看出,学与思的不同不能够孤立地去理解,它们实际上牵连着荀子和思孟各自的核心观念。学注重外向的索取,思强调内在的发掘。但这只是表面的东西,更要紧的是,对两者的侧重关涉到对生命的基本理解:或者乐观或者悲观的看法。徐复观说:“孟子认为人之性善,只要存心、养心、尽心,便会感到万物皆备于我矣;所以孟子反求诸身而自足的意味特重。但荀子认为性恶,只能靠人为的努力(伪)向外面去求。从行为道德方面向外去求,只能靠经验的积累。把经验积累到某一程度时,即可把性恶的性加以变化。由小人进而为士君子,由士君子进而为圣人,当非一朝一夕之功,所以荀子特别注重学,而学之历程则称之为积;积是由少而多的逐渐积累。伪就是积,所以荀子常将积伪连为一辞。”(徐复观,第249页)这里的观察是正确的。总的来看,孟子对于生命的理解是乐观的,认为人在根本上是善的,所以偏重内向的思。荀子不同,性恶的主张决定了其认为生命必须通过外向的努力才能获得改变。
《劝学篇》在荀子思想以及儒家思想史中的意义,在过去的研究中并没有被特别地强调。本文上述的描述和分析表明,它其实代表着一种迥然不同于子思和孟子的儒学路径。《劝学篇》呈现出来的学以致圣理路也呼应着《荀子》整部书的编排理念,并与《论语》从《学而》到《尧曰》的结构相一致。与此相对,子思和孟子代表的则是思以致圣的方向。学与思的分别并不仅仅关系到修身的方法,同时也牵涉着各自的核心主张,如对人性、人心以及天道等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劝学篇》所突出的“学”的观念,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进入荀子乃至整个儒家思想的门径。
【注释】
①《五行》:“善,人道也;德,天道也。”人道与天道的区分在这里是以是否“形于内”来决定的,由此,天和心开始有了密切的关系。沿着此路向发展,就引出了《孟子》和《中庸》里“诚者,天之道也”的说法。
②如果以《五行》作为于思的代表作品,那么其中只是提到了心,丝毫不涉及性的内容。孟子则不同,由于性善落实为良心,因此心与性已经合而为一。
③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在此段话下注云:“一说,这可能是荀况用来影射孔丘的孙子子思(名伋)的。”(《荀子新注》,第358页)梁涛《荀子对思盂五行说的批判》一文中也提到了这种可能性。(见梁涛)
④如荀子所描述的人在获得“大清明”之后的状态。此见于《解蔽篇》:“虚一而静,谓之大清明。万物莫形而不见,莫见而不论,莫论而失位。坐于室而见四海,处于今而论久远,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度,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制割大理而宇宙理矣。”
⑤其实荀子此处“仁之思”、“圣之思”的说法,从形式上说该是受也《五行》“仁之思”、“知之思”、“圣之思”的影响,但意义上有根本的区别。这也更加证实了荀子此段话和思孟的关系。
【参考文献】
[1]古籍:《史记》,《论语》,《五行》,《管子》,《孟子》。
[2]梁涛,2001年:《荀子对思孟五行说的批判》,载《中国文化研究》第2期。
[3]《四库全书总目》,1965年,中华书局。
[4]王博,1996年:《〈中庸〉与荀学、〈诗〉学》,载《国学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5]徐复观,1984年:《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台湾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