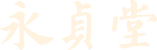一种与现实完全冲突的理想,在与现实相联系时,必然会引发出以其理想为坐标,而对现实的批判。《公羊传》以文王之正为理想,面对《春秋》所载不合于文王之正的各种现象,发出了严厉的批判,这一批判见于《公羊传》对各种不合于文王之正的讥、贬、绝中,集中地体现了《公羊传》的现实批判精神。可以说,《公羊传》的基本思想主要就是由文王之正的大一统的理想层面与对礼崩乐坏的讥贬绝的现实层面这两个方面所构成。本文仅就《公羊传》的现实批判精神作一讨论。
一、《春秋》有褒贬
《公羊传》的现实批判是通过《春秋》的讥贬绝来进行的。这里首先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公羊传》是否有褒贬,在后来的经学家那里对这个问题是有不同看法的。
治《春秋公羊》的经学家都承认《春秋》有褒贬。董仲舒说:“《春秋》采善不遗小,掇恶不遗大,讳而不隐,罪而不忽,[1]以是非,正理以褒贬,喜怒之发,威德之处,无不皆中,其应可以参寒暑冬夏之不失其时已,故曰圣人配天。”[2]司马迁说:“《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3]何休《公羊解诂》说:“《春秋》褒贬,皆以功过相除计。”[4]而刘逢禄在《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以褒、讥贬绝为三科九旨的九旨之一。清代的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说:“说《春秋》者,须知《春秋》是孔子作,作是做成一书,不是钞录一过,又须知孔子所作者,是为万世作经,不是为一代作史,经史体例所以异者,史是据事直书,不立褒贬,是非自见,经是必借褒贬是非,以定制立法,为百王不易之常经。”[5]
连不专治《春秋公羊》学的许多人都承认《春秋》有褒贬。范宁《春秋谷梁传序》说:《春秋》“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6]刘勰说:“《春秋》一字以褒贬”;[7]“昔者夫子闵王道之缺,伤斯文之坠,……因鲁史以修《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8]认为《春秋》的只言片语皆有褒贬,而且《春秋》的褒是莫大的荣耀,《春秋》的贬是最大的耻辱。刘知几也肯定《春秋》有褒贬说:“昔夫子修《春秋》,吴、楚称王,而仍旧曰子。此则褒贬之大体,为前修之楷式也。”[9]“昔夫子修《春秋》……而贼臣逆子惧。”[10]这些说法的表述虽异,但无不肯定《春秋》有褒贬。
也有的否认《春秋》有褒贬。如孔颖达在《左传序》中说:“《春秋》公羊、谷梁之书,道听涂说之学,或日或月,妄生褒贬。”[11]朱熹也反对以褒贬说《春秋》:“《春秋》只是直载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非是于一字上定褒贬。”[12]并宣称自己不相信褒贬说:“若谓添一个字,减一个字,便是褒贬,某不敢信。”[13]吕大圭的《春秋或问》卷一,有一篇《春秋褒贬论》,也反对《春秋》褒贬说。郑樵在《通志》卷四十六的《谥略第一·序论第一》中,更是认为褒贬说是对《春秋》的最大危害,他写道:“臣恐褒贬之说不已,则《春秋》或几乎息。”连被认为重视《春秋公羊》学的赵汸在《春秋属辞》的《存策书之大体第一序》中亦批判褒贬说:“为《春秋公羊》者遂以《春秋》为夫子博采众国之书,通修一代之史者,于是褒贬之说盛行,又有以为有贬无褒者,……说经昧其源委一至是哉。”[14]赵汸不仅否认《春秋》有褒贬之说,而且认为以褒贬说《春秋》是完全的误说,是《春秋》一直得不到说明的原因之一。
就《公羊传》而论,是明确承认《春秋》有褒贬的。但是,《公羊传》言褒只有一条材料,见于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是对娄仪父来鲁国的褒奖。除此以外,《公羊传》基本上没有褒的明确语言。而言讥、贬、绝的地方达到近百处,根据我的统计,《公羊传》言讥最多,约50次;贬次之,近40次;绝最少,近10次。这是由当时的社会状况所决定的,春秋时期礼崩乐坏,战国时代群雄逐鹿,旧有秩序被打破,新的社会规范尚未建立,整个社会处于动乱之中,所谓“《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15]而战国的战乱较之春秋更是有增无减。这与安定祥和的文王之治的理想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战国儒生在训解《春秋》时,只能是借讥贬绝,来体现其对现实的批判。在短短不到3万字的一部著作中,有百条讥贬绝,说明在《公羊传》的学者眼中对当时社会礼崩乐坏的深恶痛绝。
二、讥贬绝的现实批判性
讥贬绝都是对违背礼制的各种言行的批判,但是,有程度轻重不同的区分。一切不合于礼制的言行,都在讥与贬之列,而其中较为严重的情形则被列于绝的对象。讥的含义是讥刺、讥讽,是讥贬绝中最轻微的批评,是对一般不合礼的行为的讥刺。贬有贬低、贬斥之意,贬是对较为严重的不合于礼的言行的批判,较之讥的讥讽、讥刺,贬在语气上要更重一些。但《公羊传》的讥、贬有时也分得并不清楚,对同一件事,常常是讥、贬互用。如隐公三年、宣公十年(公元前599年)的讥世卿之说,既以称尹氏、崔氏为贬,又说贬是讥世卿。而在多数地方,《公羊传》言贬都是独立于讥而单独使用的,如隐公二年,贬展无骇的灭极;庄公元年(公元前693年),贬弑君杀夫的桓公夫人齐姜;僖公二十七年(公元前633年),贬执宋公的楚子;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贬废置君王的晋大夫郄缺;宣公十一年,贬专杀的楚庄王等。就贬的这些事件而言,涉及灭国、弑君、专封、专杀等,都属于礼制的重要部分。绝有绝灭、诛绝之义,较之讥、贬是最严重的批判、最严厉的责罚,而不只是“断绝爵位”,[16]《公羊传》所绝的人都是罪大恶极之人,如淫于蔡的陈君佗,[17]得罪于天子并有篡位之罪的卫侯朔,[18]诱杀蔡侯般的楚子虔等。[19]用刑法来比喻,讥是对一般犯罪的惩处,可免于有期徒刑或缓刑;贬是对较为严重犯罪的判罚,是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绝是对罪大恶极的判决,是枪毙。讥贬绝虽然有程度轻重的差别,但都是对现实的批判。而批判的尺度就是《公羊传》所谓的文王之正,而所谓文王之正,并不是周文王的已成法典,而是《公羊传》根据战国时期发展所规定具有新的时代内容的文王之正。讥贬绝虽然含义不同,但都是对现实的批判,所以,通过对《公羊传》讥的分析就可以明白其现实批判精神。
就讥的内容而言,《公羊传》所讥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对不合于礼制言行的讥刺,如隐公二年的“讥始不亲迎也”,三年,讥“武氏子来求赙”,五年,讥“初献六羽”;桓公二年(公元前710年),讥“纳于太庙”,三年,讥“齐侯送姜氏于讙”,十五年,讥“天王使家父来求车”;庄公元年,讥“筑王姬之馆于外”等等。对这些不合于礼制的讥讽,《公羊传》往往以“非礼也”的文句来作断语,如庄公二十二年的讥“肆大省”与讥“公如齐纳币”等处,皆以被讥讽的言行“非礼也”为结尾。这是《公羊传》在表述讥的时候,所运用的典型语式,在《公羊传》中总计至少有24处之多,由此可见,《公羊传》的讥是以合不合礼为其标准的。就所讥的内容而言,涉及到名分等级、婚娶、丧祭等礼制,如隐公三年,“武氏子来求赙。何以书?讥。何讥尔?丧事无求,求赙非礼也,盖通于下”;桓公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来聘。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仍叔之子何?讥。何讥尔?讥父老,子代从政也”;庄公二十二年,“冬,公如齐纳币。(传)纳币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亲纳币,非礼也”等等。这些地方所讥刺的非礼,都是指不符合周礼的言行,所以,这些讥刺带有维护周礼的性质。
但是,《公羊传》并不是完全维护周礼,也有否定周礼的地方,如隐公三年,释“尹氏卒”:
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尹氏何?贬。曷为贬?讥世卿,世卿非礼也。[20]宣公十年“齐崔氏出奔卫”一条,《公羊传》亦有同样的解说:
崔氏者何?齐大夫也。其称崔氏何?贬。曷为贬?讥世卿,世卿非礼也。[21]世卿世禄原本也是周礼的规定,可是《公羊传》却不止一次地说世卿非礼,予以讥刺。这一观念是对春秋战国时期社会阶层分化的历史变化的承认,否定了分封制下世卿贵族的特权的合理性,肯定了取代世卿贵族的新兴社会阶层的合法性。所以,世卿非礼不仅含有反对古代分封制的世卿世禄制度,而且带有承认新兴社会阶层的合理性的意义。可见,《公羊传》反对周代以来的世卿世禄制度,所要维护的礼,已经不完全是孔子所说的周礼,而是包含新兴社会阶层利益的礼。
《公羊传》所讥的另一大类内容,是对当权者只顾自己的骄奢淫逸,而不顾人民死活的言行的批评。如隐公五年,讥“观鱼于棠”;桓公四年,讥“公狩于郎”;八年,讥本应于冬祭的“春烝”;庄公二十八年,讥“臧孙辰告籴于齐”;二十九年,讥凶年“修旧”;三十一年,讥“筑台于郎”、“筑台于薛”与“筑台于秦”;成公十八年(公元前573年),讥“筑鹿囿”;定公二年(公元前508年),讥“新作雉门及两观”等。这些讥讽既是儒家要求统治者应该洁身自好,爱民如子,反对统治者的骄奢淫逸,也是主张给人民的生活以一定保障的体现。它是自孔子以来儒家民本观念在《公羊传》的体现。所以,《公羊传》特别反对增加人民的负担,在宣公十五年论及“初税亩”时说:
初税亩。初者何?始也。税亩者何?履亩而税也。初税亩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履亩而税也。何讥乎始履亩而税?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颂声作矣。[22]初税亩无疑是古代税制的一个进步,《公羊传》采用讥刺的态度是不恰当的。但是,《公羊传》在这里提出统治者对人们征收赋税的标准是十分之一,指斥不符合这一标准就是桀纣与豺狼,其所批判的对象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统治者。当时的统治者为了在群雄逐鹿中获得胜利,也为保持自己骄奢淫逸的腐化生活,征收人民的赋税远远超过十分之一,有的甚至达到了三分之二,如《晏子春秋》说:“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积朽蠹,而老少冻馁。”[23]尽管《公羊传》的什一而税带有理想的色彩,但什一而税确有减轻人民的赋税,批判统治者贪得无厌的积极思想成分。什一而税的说法,出于孟子,《孟子》中不仅数次谈到什一而税,并在《孟子·告子下》说:“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24]这说明,孟子的思想与《公羊传》形成确有紧密的联系。《公羊传》不仅认为什一而税是尧舜之道,而且认为是“天下之中正”,这是要为整个社会确立一个通行的公平的赋税尺度,既保证统治者的合理需求,又给人民的生活以一定的保障。按照何休的解释,鲁宣公实行“初税亩”,是以最好的田地为标准来实行税收,无疑是对人民的残酷剥削。所以,《公羊传》的讥刺“初税亩”带有反对春秋战国时期统治者过分剥削人民的积极意义。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94年)的“讥始用田赋”,[25]也具有这样的意义。
由《公羊传》对统治者不顾农时,一味地沉溺于田猎游乐、修筑宫室,及其不顾人民生活的横征暴敛这一系列的批判来看,《公羊传》秉承了从孔子、孟子以来的儒家对人民的某种重视。人民在社会的底层,在连年战乱不断的战国时期,人民的处境更是水深火热、朝不保夕,《公羊传》的这一思想具有同情人民,给人民一定社会保障的积极意义,它既是儒家重民思想在战国的发展,也成为西汉春秋公羊学的重要思想成分。
三、讥贬绝的原则与方法
《公羊传》的讥贬绝并不是对春秋执政者所有罪恶的揭露批判。《公羊传》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说:
《春秋》不待贬绝而罪恶见者,不贬绝以见罪恶也。贬绝然后罪恶见者,贬绝以见罪恶也。[26]与犯罪的情况类似,有的犯罪一目了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用公安机关侦讯就可以结案,而有的犯罪较为隐晦,必须经过公安机关侦讯才能结案。《公羊传》所批判的不合于礼的现象也有两类,一类是不需讥贬绝,就可以明显看出其不合礼的罪恶,对此《公羊传》就没有讥贬绝必要;另一类是需要讥贬绝,才可以将其不合礼的罪恶揭露出来,这个时候《公羊传》才采用讥贬绝。所以,《公羊传》的讥贬绝并不是对所有罪恶的无遗漏的批判,而只是对其中部分较为隐晦罪恶的揭露。
与此说相近的是“壹讥”之说,庄公四年“冬,公及齐人狩于郜”,《公羊传》说:
公曷为与微者狩?齐侯也。齐侯则其称人何?讳与仇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后此者有事矣,则曷为独于此焉?讥于仇者将壹讥而已。故择其重者而讥焉,莫重乎其与仇狩也。于仇者则曷为将壹讥而已?仇者无时,焉可与通,通则为大讥,不可胜讥,故将壹讥而已,其余从同。[27]鲁庄公与齐侯有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根本不应该与之交通,若是与之交通,就已经是应当大讥的行为,与之一起狩猎,更是错上加错。而鲁庄公与齐侯的交通是经常的,所以,要讥刺就会讥不胜讥,而只能选择最严重的事件,进行“壹讥”,也就是一次的讥刺。但一次讥刺并不代表只是讥刺一次,而是与之相关的违礼行为都在讥刺之列。所以,必须将讥贬绝与不待讥贬绝的两个部分结合起来,将“壹讥”与不书之讥结合起来,才可以看出春秋当权者的所有罪恶,准确认识春秋的礼崩乐坏的严重情况。
《公羊传》的讥贬绝有一个重要原则,是所谓“疾始”。如隐公二年、八年的“疾始灭也”,隐公四年的“疾始取邑也”,隐公五年的“讥始僭诸公”,桓公七年的“疾始以火攻也”等等,皆以“疾始”为说。《公羊传·僖公十七年》说:“君子之恶恶也疾始,善善也乐终。”[28]“疾始”是对各种罪恶开始所表示的极大愤恨,也含有希望将罪恶消灭在开始之义。所以,“疾始”所“疾”的事件与人物,都受到《公羊传》的严辞痛斥。如《春秋》最早记载灭国的是鲁国大夫展无骇,当展无骇在隐公八年去世时,就只说:“无骇卒”。《公羊传》说:“此展无骇也,何以不氏?疾始灭也,故终其身不氏。”[29]认为《春秋》对展无骇的直呼其名,而不称其姓。是因展无骇帅师消灭极国,而对他的谴责。据庄公十年,《公羊传》对蔡侯献舞的直呼其名的解释:“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蔡侯献舞何以名?绝。曷为绝之?获也。曷为不言其获?不与夷狄之获中国也。”[30]从这里可见不称其姓,在讥贬绝中属于绝的范围,是一种最为严厉的谴责。
值得注意的是《公羊传》“疾始”的“始”并不是真正的开始,而是《春秋》所托之始,《公羊传》隐公二年,在贬展无骇灭极时说:
无骇者何?展无骇也。何以不氏?贬。曷为贬?疾始灭也。始灭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则曷为始乎此?托始焉尔。曷为托始焉尔?《春秋》之始也。[31]《春秋》的“托始”,是指《春秋》记载中最先出现的罪恶,而不是罪恶的最先开始,故《公羊传》言疾始基本上都在隐公、桓公之年。所以,《公羊传》的“托始”说,并不是对罪恶出现开始时间的追寻,而是表达对罪恶开始的疾恶如仇,带有将罪恶消灭于萌芽的方法论意义。某一罪恶的开始很难追寻到最先的源头,但可以通过“托始”的方式,来给罪恶界定一个开端,并以此表达将罪恶消灭于萌芽的观念。这对后人训解《春秋》具有很大的影响。从“托始”发展开来,可以把《春秋》的文辞都说成是孔子理想的寄托,不同的人都可以借一个“托”字,对“所托”作出自己的阐发,以发挥出适合自己需要的观念。历史上的许多经学思想家就是借助这一方法,来创立自己的思想体系的。
《公羊传》通过讥贬绝对春秋时代不合于礼义的行为的批判,是一种现实的批判,孟子的乱臣贼子惧之说绝不是偶然的。这一精神也是中国文化最宝贵的财富,每当中国历史走入黑暗之时,总会有一批有志之士不顾个人安危,奋起批判社会的黑暗,而给社会带来光明的理性曙光。
【注释】
[1]原文不存,钟肇鹏主编以为所脱两字似乎当作“明察”(见《春秋繁露校释(校补本)》下册,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7页),其说可据。
[2]董仲舒:《威德所生第七十九》,《春秋繁露》卷17,钟肇鹏主编《春秋繁露校释(校补本)》下册,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5~1076页。
[3]司马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史记》卷130,《四库全书》本。
[4]《十三经注疏》下册,(清)阮元校刻,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233页。
[5]皮锡瑞:《论春秋是作不是钞录是作经不是作史杜预以为周公作凡例陆淳驳之甚明》,《经学通论》卷4,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页。
[6][11]《十三经注疏》下册,(清)阮元校刻,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359、1703页。
[7][8]刘勰:《文心雕龙》,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169页。
[9]刘知几:《史通·内篇·称谓第十四》,浦起龙:《史通通释》卷1,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版,第13页。
[10]刘知几:《史通·内篇·载文第十六》,浦起龙:《史通通释》卷1,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版,第6页。
[12][13]朱熹:《朱子语类·春秋》卷83,《四库全书》本。
[14]赵汸:《春秋属辞》卷1,《四库全书》本。
[15]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卷130,《四库全书》本。
[16]平飞:《〈公羊传〉“以义解经”的特质发微》,《孔子研究》2008年第4期。
[17]《春秋公羊传·桓公六年》。
[18]《春秋公羊传·桓公十六年》、《春秋公羊传·庄公六年》。
[19]《春秋公羊传·昭公十一年》。
[20][21]《十三经注疏》下册,(清)阮元校刻,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204、2283页。
[22][24][25][26]《十三经注疏》下册,(清)阮元校刻,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287、2761、2351、2316页。
[23]晏婴:《晏子春秋·内篇问下第四》卷4,《百子全书》上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48页。
[27][28][29][30][31]《十三经注疏》下册,(清)阮元校刻,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227、2255、2210、2232、22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