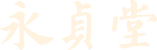根据船山的看法,宇宙的本源是太虚中的絪缊之气,气聚而生成人物,人物死而散为气而归于太虚。聚散、生死是自然变化的必有之几。气聚为人而可见,这是“明”;人物死散而归于太虚,不可见,这是“幽”。所以从生到死,是从“明”转变为“幽”,而不是从“有”消灭为“无”。
如果船山仅仅停留在这种看法上面,那么他与张载的思想就完全相同,仍然是一种不同于佛教和道教的自然主义的生死聚散说。就反驳佛道教、坚持自然变化的辩证观念而言,此说相当有力;同时,作为一种宇宙人生观,视生死变化为自然,不惧不畏不留,也有其重要的人生指导意义。
然而,若进一步问,在这种生死观下,人的善恶对“生”有何意义,对“死”有何意义,那么仅仅停留在以聚散释生死的观念上,就无法回答了。当然,船山认为从自然的健顺之性而继之为仁义之性,以说明人的道德本性根源于天地之性,以确证善的根源,这也在一个方向上把他的气体—气化的宇宙论与善恶问题连接起来。但船山实际上未止于此,与张载区别的是,他的宇宙论的特色和思想特质最终要在善恶对于生死的意义上表达出来,善恶对宇宙的意义亦成为船山思想的终点。这就是“存神尽性,全而归之”。
一
王船山认为,张载《正蒙·太和篇》的宗旨,是在于“存神而全归其所生之本体”,实际上这也就是船山《正蒙注》的宗旨。“存神”是君子的功夫,“所从生的本体”就是人的身体和生命的来源,在船山就是指太和絪缊。换言之,《太和篇》的宗旨是要人以存神的功夫以达到死后全部地归返于太和本体。这样一来,船山《正蒙注》的重点就转到了“功夫—本体”,而“生死—善恶”的问题便构成为船山思想的核心问题。我们在后面会看到,“存神尽性”、“全而归之”在船山晚年已经成为其思想体系中的“终极关怀”。
船山强调,人如果不能知生知死,不能对生命的根源与死亡的归宿有完整了解,那就不能了解善恶的意义,不能理解为善去恶是人性固有的当然,从而会认为善恶的分别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以为为善去恶不是人性固有之当然,善恶分别是没有意义的,那就会导出三种不良的发展:一是纵欲主义,抛弃一切伦理规范以追求个人的私利;二是虚无主义,认为善恶对于人的生命是多余的,人生的一切在死后都消灭无余,所以生命和善恶都没有意义;三是“自由主义”,追求生活的无规范无拘束,随心所欲,而最终变成为一种猖狂的人格形态。第一种人即世俗小人,第二种人即佛老之徒,第三种人指王门末流。所以,对宇宙和生命的“原始反终”,其根本目的是使我们能够确认“善”是本性所固有,“为善”是我们天生的责任,认识到生命为真实,死亡不可怕。
船山指出,《正蒙》解决这一问题的进路是,确认阴阳变化宇宙的实体基础,屈伸生死是自然的普遍法则;阴阳和屈伸是人道大经的本源,人道是从阴阳屈伸中得以引申出来;从而,人的言行及人生的一切都在气化聚散之中而不会消灭,也都在天道皇皇的流行之中而受其往复,对生时的善待便是对死后的善待,生时的善对于死后有影响、有作用;如果明白这些道理,就能真正了解“存神尽性”是人性的良能,人生的当然。
在船山看来,如果不能认清《正蒙》的道理,生命就没有价值目标,一切价值如同大海的泡沫,人就不能“安身立命”。可见,船山的思想的要旨是要立基于儒家的生死观和善恶观来解决人的“安身立命”的问题。船山的思想,在一定的意义上看,具有自然主义的特点,因为他要把善恶的问题追溯到自然的生死,追溯到阴阳的屈伸,试图以阴阳屈伸的自然来说明价值的根源。但是,在基本出发点上看,其基本关怀是人道的、价值的,所以尽管他对善恶根源的哲学论证诉之以气学的形态,但船山思想在总体上又不能简单归结为自然主义,更不能归结为一种与人文价值无关的自然辩证法。
二
在《正蒙注》中,船山继承了张载的思想,以气的聚散来说明生死的本质。在他看来,气聚合而成人成物,这是“出而来”;人与物生命结束,气散归入于太虚,这是“入而往”。气有聚散,人有死生,这是自然变化的法则,也是永恒的势运,决无停止之时。因此,人不能以为个体的生命身体是能够永久不死的。生死聚散有自己的规则,君子的态度是顺应它,安于生,安于死,平静而自然地接受生死变化。人对于气化聚散生死的过程是无所作为的,人所能够作的,就是以“俟命”的态度顺其自然,而无所恐惧留恋。当然,船山在这里并没有表达全面,人对于生死,不仅应以俟命的态度对待,还要尽力于心性的修养,这一点船山在其他地方多次加以强调。
船山也继承了张载关于鬼神的说法,张载说“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船山说:“鬼神者,气之往来屈伸也。”(《乾称》)“阴阳相感,聚而生人物者为神,合于人物之身;用久则神随形敝,敝而不足以存,复散而合于絪缊者为鬼。”(《太和》)古代宗教以人死后的存在为鬼,船山认为人物之死,即消散为气,还归于太虚絪缊之中,所以死散之气可名为鬼。反过来说,宇宙中并没有别的鬼,鬼就是死散而归向太虚的气。他又认为,太虚之中的神是一种变化的内在动力,它使得阴阳聚合为人物;而人物生成的时候,太虚之神就合于人物之身而成为人物的神智之神。
船山也指出,神是无所谓“聚”,也无所谓“散”的。聚散是气,屈伸是指形气,神则无所谓屈伸,神也无所谓幽明。神本来是形而上的,太虚之神和人物之神,都是不可象的,所以无论形象如何聚散,神是无所谓幽明之分的。当然,神随着气之散,也会返于太虚。对此,船山也从理气的角度加以说明。他认为,事物的理,在事物未聚合成形以前,是作为太虚的体性,天的体性。当气聚结为人为物时,原来天的体性就转而成为人物形体中的性理。人物死而化气弥散,理也就重新回复为气的理,而随气返归于太虚。
但是,船山与张载的一大不同是,在张载,“散入无形,适得吾体;聚为有象,不失吾常”(《正蒙·太和》)是自然的,与人为无关的,描写的是自然生死聚散的循环过程。但在船山,则强调“适得吾体”和“不失吾常”都有人为的因素参与其中,这也是船山思想的要妙之处。在船山看来,以至诚的修养使自己与太虚絪缊保持一致,以存神的修养使自己与太虚神化的良能一致,如此,才能“生而不失吾常,死而适得吾体”。
这一“死而适得吾体”,在船山更表达为、诠释为“全而归之”。正如我们在前文所指出的,船山最特别的地方,是他指出《正蒙·太和篇》的宗旨是“存神尽性,全而归之”。“全而归之”的“归之”,当然是归于其本体,这本体就是太和絪缊。与张载不同,船山所说的“全归”很有讲究,体味他的话,人并不是在死后便可自然地“全归”其所从生的本体,“全归”实是“存神”修养的结果,这就是说,有存神的功夫才能全归本体,没有存神的功夫则不能全归本体。也就是说,有存神的功夫才能生时“不失吾常”,有存神的功夫才能死后“适得吾体”。“适得吾体”即回到、保有原来的状态。
人在生时若能尽性行道,则其生异于禽兽之生,其死也异于禽兽之死,这种异于禽兽之处乃在于他能“全健顺太和之理以还造化”。“还”就是“归”,这就是“全而归之”的意思。在船山这段话里,我们应当注意,按照他的说法,如果我们不能尽性存仁,就会影响太虚的本体,就不能全健顺之理还归造化。只有我们在德行上做到“与太和絪缊本体相合无间”,我们才能够“全而生之,全而归之”。而“全而生之,全而归之”就成为我们的目标和目的。所以船山要强调“此篇(注:指《太和》)之旨,以存神而全归其所从生之本体”,存神在这里有着重要的作用,它决定着一个人死后如何回归,能否“全归”。
三
究竟什么叫“全而归之”,它和人的善恶有何关系?船山认为,气聚成形,形散为气而还归太虚,气仍然回复为其自身。神与气不相离,气回复为自身,神也依旧还是气之神(从形之神回复为气之神)。换言之,聚结为人物的气,在人物死亡而消散之后,并非消散为无,而是复归于本然的絪缊。形体的神本来来自气的神,形体散为气以后,形体的神也没有变为为无(本无聚散),也只是回复到作为气之神。神者气之灵,是指形体的神,即神是气的虚灵作用和功能。这些都是强调气、神在散归后并没有消尽为无,气仍然作为气存在着,神仍然作为神存在着。人生在世时的善或恶,治或乱,在人死之后,依其类而归散为气。善气和恶气各依其类而散,善气散归入善气类中,恶气散归入恶气类中,互不混淆。这是一种很奇特的思想,这既不是纯粹的自然主义,更不是纯粹的人文主义,而是带有某种宗教或神秘色彩的气学世界观,这很可能与明代后期、明末的善恶报应论和民间宗教的死后观念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
人生善恶对宇宙的影响,不仅在于死后的归类,而且在其生前。不仅人在死后散为气对宇宙有影响,即使人在活着的时候,他的行为的善恶都会随时成为一种气或者与气一起而游散于天地之间。这些言行的善恶与气一起,结为一定的天象气候,影响人的社会生活,如所行之善在天地之间结为祥瑞,所行之恶则结为灾害。这些也属于鬼,是未死前的鬼。
在这样的宇宙观下,人在生时的言行善恶,并不仅仅是一种名声,一种社会评价,也决不会象大海的泡沫消散灭尽,反而,在他的生前和死后,都会变成为宇宙当中的一种实体性的存在,影响天地两间的气象,影响宇宙的构成。就本质而言,这类思想在历史上至少可以追溯到西周伯阳父和汉代的灾异感应说,甚至有佛教“业”的影子。在船山看来,从理论的功能上说,如果主张人们的善恶行为随一死而消散无余,那么人们就会认为,圣贤和盗贼,大善与大恶,归宿完全相同,他们的分别没有意义。从而就会使人无所畏惧,无所顾忌地走向纵欲主义。君子知道人们的善恶行为不会随一死而消散无余,因此修身俟命,存神尽性,这样生时全面行善,与太虚通为一体,不会留下任何浊气灾眚于两间之中,这就是“全而生之”。这样的君子死后合于太虚,以全清之气回归到絪缊太和,这就是“全而归之”。他认为,所谓周孔万年,所谓文王在上,都应该从这个方面来理解。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说,王船山思想的落脚之处,现在已明白无遗。这个生死——善恶的问题是船山晚年思想的核心和要义,其他的复杂的理论辨析和概念组织都是围绕此一核心的外围建构和展开,或为这一落脚点所铺排的理论前提。他的所谓“气论”也不可能离开这一点来理解。这种观念不仅受到宋明理学的明确影响,也可能受到明末善书和民间宗教等流行的善恶报应论的刺激,而他的奸回、灾眚的说法也应当饱含了他所亲历的明末的社会动乱与天崩地解的经验。
就船山的说法来看,他的表达不是完全周全的。照船山的宇宙论的逻辑来说,人死后,不论其生前行为如何,其气应当不会挠太虚本体而为之累。因为,如果桀纣之气留在太和氤氲之中,则太和之中便有浊恶之气,这是不合其宇宙论的。因此,人死形亡之后,清浊犹依其类,应当是指“两间”而言,而既然人从太和带来的气有一部分变为“客感杂滞遗留两间”,人当然就无法“全而归之”于太虚本体了。
从这点来看,“全生全归”虽然说的是个体,但其善恶似乎更多地落脚在社会的治乱上,善恶之气在两间,所影响的主要是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船山此说并不是着眼在个体的报应,而是对社会治乱的一种解释。这显然是由明末社会大动乱所引起的思考和哲学解释。在这种解释中,人的善恶行为可以变为具有实体意义的气,对社会、历史造成影响。
余论
船山思想的主题,以其晚年的《正蒙注》为代表,通过“全而归之”体现了他的终极性的关怀,这一点,从他的自题墓铭“幸全归于兹丘”中的“全归”二字也可得到证明。船山的所有努力,是以强烈排击佛老的姿态,谋求全面树立儒家圣学的世界观,这与道学兴起的主题是一致的,故船山的思想主题可说仍然延续着道学的主题。所不同的是,船山对佛老影响的忧虑是历经了明末社会和思想的变化而有感而发。但不论其所发之外缘如何,在思想和理论上与道学的主题仍为一致。船山的思想要排除佛老的影响,破除二氏的虚无主义宇宙观与人生观,试图建立一宇宙论的通贯解释以安立儒家的人性论、实践论,并以此以为儒学正统的重建,彻底破除佛老的迷蒙。
除了善恶对社会历史的意义外,“全而归之”的论述,显示出船山思想中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即人对于宇宙的责任意识,而所有的意义都是建构在这一责任意识上的:人对于宇宙的原生生态的保持和净化,是一件具有根本意义的事情;人要以善生善死来承担起他对宇宙的这种责任。船山把这样一种意识作为其整个思想的基础和目标,这不能不说是相当独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