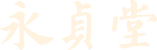■传统戏曲生存艰难,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即是戏曲自身没有及时完成向现代审美的转化。戏曲的“现代性”不是时间概念,而是一种价值取向和品质认同
■重返城市是说曾经拥有城市,而后逐渐疏离了城市,不能与城市审美同步而行,因而不得不淡出城市,结果则意味着戏曲越来越丧失了在城市文明中的竞争力与影响力
■我们今天所称的传统戏曲,主要是在过去的戏园、茶楼、庙台、广场等简陋的民间演出场景中形成的表演艺术形态,而今天它的演出场所已经转移到了城市化规范化的现代演艺空间。传统戏曲既要在相适应的场所展示自己,也要自觉登上包括大剧院在内的各种新兴演出场所与传播平台,加快实施“转化创新”意义中的“换形”
每年不少于一个戏曲剧种正在消失
戏曲是什么?国务院颁布的《扶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文件,对此作了明确界定,戏曲是“表现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就是说,戏曲不是简单的娱乐,不是简单的商品,也不是简单的宣传工具;戏曲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是中国人的人格图谱,中国人的精神DNA。许多年来,戏曲一直没有获得身份认同,所以它的价值感一直是模糊的。有一个时期,戏曲被当成包袱,必欲推入商海自生自灭;抑或又拿它当作宣传工具,仅作敷演英雄模范、表彰好人好事、图解时势政策之用,不顾及它的内在特质; 抑或又将之视作赏品、玩意儿,拿几段耳熟能详的唱段侍应娱乐豪门,跑场子、窜堂会、凑晚会。事实证明,凡是将戏曲简单地视作娱乐、商品或宣传工具的时候,都不是戏曲健康发展的时期。
笔者认为,中华戏曲的文化传承价值与当代审美价值,至少存在于四个方面。
第一,戏曲是地域文明的延伸。中华文明的丰富性和包容性是建立在多民族多地域的文化背景下的,古老的文明,远去的历史,曾经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先人们在这方沃土上的知识创造与精神追求,随着时间的流转,已经如盐入水般溶解在包括戏曲艺术在内的各种文化形态中。历朝历代华夏儿女于海内外迁徙繁衍,足迹所到之地,也带去了长期养成的习俗,这些习俗又与所在地的文化融合,交融出新的文明。可以说凡世界各地有华人居住的地方,就有中华文明的传播,而戏曲又是综合的、活态的传播方式,所以保护中华戏曲的传承发展就是保护中华文化基因。
第二,戏曲是民众情感的慰藉。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表情和声音,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气质与品位,这种地方神采与城市气质,最能准确表达和深刻传达出生长于那个空间区域里普通民众的普遍情感。无论人生路途是否顺遂,无论现实生活是否称心,也无论是在异乡漂泊还是在故乡守望,方言乡音永远是最便捷的人际沟通渠道和情感慰藉良方。身在异国的游子,外出打工求学的子弟,一旦听到家乡戏曲,就会有一种难以名状的亲切感,就会有一种揪心的乡愁。无论何时何地,血浓于水的亲情乡情与族情,永远都是联系彼此感情的心灵纽带,也是爱国精神的具体体现。
第三,戏曲是经济发展的体现。任何一个经济繁荣的时期,任何一个社会进步的阶段,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检验指标就是看那个时代的文学艺术包括戏剧是否取得了同步的发展。中国的周秦汉唐、宋元明清,西方的希腊文明、文艺复兴,文学艺术与戏剧在一个时期的繁荣兴盛无不依托于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和富庶发达的区域。中华戏曲在中国崛起的新近30多年里从没有缺席,中国戏曲人理应分享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与此同时,戏曲还将继续参与并见证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戏曲艺术存在的本身就是在体现经济发展的程度,并且同步创造着经济与文明增长的价值。
第四,戏曲是社会进程的缩影。有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戏曲。有什么样的地方,也就有什么样的声腔。一方面,戏曲与时代同行,戏曲用艺术的声音和艺术的形象及时传达着时代的风貌和时代的感情; 另一方面,戏曲又记录着时代,把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风貌和时代特征用戏曲作品凝聚起来,传播开来,传递下去,使得今人与后人能够不断看到存在的现实和历史的情感。因此,凡是健康存在着的戏曲艺术,往往都承载着那个时代的记忆,浓缩着那个时代的情感,并成为社会进程里活的风景和活的档案。
据权威机构统计,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戏曲剧种平均以每年不少于一个剧种消亡的速率加速着衰亡的进程。消亡就是无可挽回的永久失去,是那一种曾经活跃的剧种永久消失了声音和表情。每个消失了的剧种背后是什么?是一方水土所养育的人曾经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人际之间的交流方式,是一个地方住民的方言、声腔以及人格化的、个性化的表情。这些精神和心理层面的东西就是文化,它不是用简单的娱乐、商品或者宣传工具功能所能够涵盖的。
戏曲的“现代性”不是时间概念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背景、来路、籍贯和族群,在不知不觉中都带着各自的文化基因,而戏曲就是我们对于文化传统、族群记忆的最好保存方式之一。一种方言传递一种神韵,华夏民族有那么多族群,靠什么记录他们的文化?往往靠生活习惯、靠方言以及方言延伸出来的声腔。用哪种声腔唱戏、用哪种语言说话,我们闭着眼睛就能想起那种气质。如果这些文化符号都没有了,如果我们到了中原听不到豫剧,到了西北听不到秦腔,到了安徽听不到黄梅戏,到了苏州听不到昆曲、评弹,而满耳朵灌进来的都是标准普通话演唱的流行歌曲,我们会缺少对地方的认同,甚至会有一种恍然不知身在何方的错置感。相反,所到之处都伴随着方言和戏曲,哪怕置身在千城一面的现代城市建筑中,仍然会在城市森林的缝隙间捡拾到过去城市生活的余韵。
以扶持戏曲艺术的传承发展作为复兴民族传统文化的杠杆,有助于我们重新意识到寻找文化身份的重要性。曾几何时,地方戏曲受到轻视甚至歧视,偌大中华,仿佛只需提倡一种身份,那就是只会讲差不多的话,听交响乐,看芭蕾舞,想方设法、争先恐后地要将不同出身背景的地域趣味过滤掉,以融入一种所谓的共性。在此肤浅的认识下,戏曲,尤其是地方戏曲遭受了太多不应有的挫折与刁难。如今看来,一些受伤受损的剧种或剧团很难在较短的时期内恢复元气。
回望戏曲在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中的步履,戏曲在不断坚守着自己的同时也在不断放弃着自己,有的剧种甚至不愿意讲自己的方言。上世纪八十年代,戏曲急于摆脱危机,急于创新,有些创新就是旗帜鲜明地要“让自己不像自己”,而对地方戏曲来说,首当其冲需要隐藏起来的就是方言与声腔,所以那时节的戏曲理论话题主要围绕着像与不像,京剧要不要姓京、川剧要不要姓川、越剧要不要姓越都成了问题。现在回想当初的讨论,似乎有几分幼稚,但是仔细想来,我们对于戏曲尤其是地方戏曲的确经常失去信心。如今,我们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了戏曲剧种个性的可贵,我们的创作也从努力使自己不像自己回归到努力使自己更像自己,从不像到像乃至到更像,其隐藏在创作行为背后的心理,正是戏曲人由自卑向自信的转化。
戏曲的“现代性”不是时间概念,而是一种价值取向和品质认同。现代题材甚至现实题材的作品不等于具有现代意识、具有现代性,相反,表现古代题材历史故事甚至上古神话,有时反倒充满现代感与现代性。
明朝作家汤显祖的《牡丹亭》在今天看来就充满了现代性。剧作所颂扬的价值取向是对人和人的本能欲望的尊重,与我们看到的传统戏包括许多现代戏的观念大不相同。我们无法想象在那个“存天理,灭人欲”甚至还伴随着文字狱的年代,能有汤显祖这样的剧作家,创作出这般真实的作品。这部作品就是放在今天仍然是非常现代的,它表现一个少女的第一次性幻想,表现了性别觉醒,杜丽娘为此可以经历生死而无悔无惧,汤显祖由此颂扬了人性的伟大和人的生命意识的崇高。
《牡丹亭》到现在仍不过时,不存在语言的、国界的理解障碍,因为它触及到了普遍的人性,所以具有永恒的审美价值。反观我们创作的一些现实题材作品,反而不具有这样的现代品性。有些现代戏,其所表达出来的理念还不及古人“现代”。随着非遗保护意识的加强,戏曲反倒有些刻意谨守传统,只要是前人的东西就一定是好的,只要热衷于敷衍老戏就一定是有价值的。殊不知大量的传统老戏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极不尊重女性、极不尊重人的权利,与现代文明意识格格不入。今天我们要完成对传统的转化,就是要实现有甄别、有选择、有改造的“扬弃”。戏曲创作必须服务于现代人,与现代观众产生共鸣,才能产生具有现代品格的作品。
传统戏曲生存艰难,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即是戏曲自身没有及时完成向现代审美的转化。现在许多年轻人以为传统戏曲就是夸张的脸谱、就是小嗓子演唱的声腔,就是杂耍,完全忽略了戏曲形式之内的生活内容和精神内涵,忽略了戏曲首先是用来与人沟通与人交流的文学艺术形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戏曲曾经在一种共识之下积极发展,那就是“传统戏曲的现代化”与“地方戏曲的都市化”。现代化不是要颠覆传统藐视经典,都市化更不是要阳春白雪脱离大众,而是正视戏曲所面对的生存时代,提倡戏曲自觉实现自身的价值更新与审美转化。
有必要提出让戏曲“重返城市”
今天,戏曲有必要提出“重返城市”的理念。重返城市是说曾经拥有城市,而后逐渐疏离了城市;疏离了城市说明已经不能与城市审美同步而行,因而不得不淡出城市;淡出城市的结果则意味着戏曲越来越丧失了在城市文明中的竞争力与影响力。
中国戏曲最繁荣的时期是在与城市文明相融洽的时期。元杂剧的繁荣是因为它占据了当时的京城大都,明清传奇的兴盛是因为它依托着江南一带经济富庶的商业都会,京剧的兴起是因为四大徽班涌进了京城。黄梅戏从湖北黄梅县流入安徽当时最大的码头城市安庆,而后唱进上海,在上海华东戏曲研究院的京昆和话剧专家的帮助下,从黄梅调转化为了黄梅戏。越剧,原来也不叫越剧,进入上海时,有的称绍兴文戏、四明文戏,有的称绍兴女班、的笃班、小歌班,最后才由上海《申报》统称之为越剧。就连京剧也是在当时“远东第一大都会”的上海被叫出名的。此外,诸如淮剧、扬剧、锡剧、甬剧也都是在上海都市的繁华商演中逐渐成形并被确定了剧种的名称,这些都是戏曲进城的结果。应该说,全国各地方剧种的成长成熟经历也都大致相仿,没有进城之前,它的舞台可能是庙会,可能是广场,可能是草台,但都是简易的;进入城市尤其是进入大城市后,戏曲逐步登上了20世纪的镜框式舞台,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综合性程度很高的剧场艺术,由此迈进了中国戏曲的新时期。
回望历史,我们不能忽视戏曲的每一个繁荣时期,都是以城市为标志的,不仅中国如此,外国也是如此。古希腊、古罗马的戏剧,莎士比亚的戏剧、印度的梵剧和古歌舞剧都是在当时那个国家的首都或商业大都会完成,然后形成了一个时期的戏剧形态,再向周边中小城市和乡村的市场辐射,同时享受在城里形成的戏剧成果。现在我们一说下乡,就是简单的为农民服务,就是大篷车或简易的土台演出,好像下乡就等同于轻装简从,等同于老戏老演、老演老戏,等同于将就而不是讲究,有意无意、有形无形中把农村演出当成了广场艺术的演出,把送戏下乡与艺术简陋简单地画上了等号,这是一种将戏曲演出市场与艺术发展方向相对立的简单思维。
进入新世纪的这十几年,由于理论上模糊了方向,因而戏曲艺术的整体发展缺少了方位感与方向感,本体上进步不大,收获有限,因而寄望于戏曲人自身,首先是戏曲理论评论工作者跟上步伐,作出判断,给出戏曲发展的理论方略。比如在看待传统戏曲与当代都市的关系方面,也需要滤清认识。尽管戏曲的繁盛是在各个朝代的首都或是商业中心城市形成发展和繁荣的,但那个时候的城市是农耕时代的城市,它是以农业文明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为标志的。如今,当我们乘坐在纵横交错的城际高铁上,巡视窗外,无论从东到西,由南向北,沿途已经很难看到记忆中的乡村,映入眼帘的都是城镇化了的新农村景象,小楼、别墅、标准化的田园和集体化的住宅,住宅的顶上安着太阳能装置、竖着电视接收天线,即便是绿地也是城市化了的美化了的绿茵。整个中国社会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娱乐方式以及审美趣味都处在快速城镇化、城市化、都市化的进程中。以农耕时代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交流方式为依托的戏曲艺术,是不是因为我们重视了它,它就一定能够如我们所愿,自然而然地融入现代社会中,它是不是也同样需要实施由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的时代转型和审美转化?事实上,传统戏曲的生存危机主要是在城市剧场演出的危机,我们在鼓励“送戏下乡”的同时,首先应该鼓励“站稳城市”。
我们今天所称的传统戏曲,主要是在过去的戏园、茶楼、庙台、广场等简陋的民间演出场景中形成的表演艺术形态,而今天传统戏曲的演出场所已经转移到了城市化规范化的现代演艺空间。表面上看,演出场所与表演形态似乎没有关系,其实关系很大,有什么样的演出空间就有什么样的演艺形态,有什么样的演艺形态就有什么样的演出场所。时至今日,中国舞台艺术的主体形式仍然还是戏曲,然而全国各地正在热火朝天建造的大剧院、歌剧院仿佛又都与戏曲演出无关。是让变化的剧场适应不变的戏曲,还是让戏曲在变化中适应不同的剧场,我想戏曲既要在相适应的场所展示自己,也要自觉登上包括大剧院在内的各种新兴的演出场所与传播平台,以适应现代演艺环境的变化。戏曲进入大剧院演出,并不意味着大制作或人海战术,而是要有足够的气场与能量支撑起庞大的空间。为此,戏曲的创作必须跟上,简单地把戏曲传统戏放置在大剧院的环境中演出,不但显示不出传统戏曲艺术的精妙,反而会显得单调简陋,与现代剧场演出环境格格不入。二十一世纪大剧院建筑在中国的兴建,对中华传统戏曲演出来说是增加了难度,也是挑战,更是机遇,它倒逼戏曲在“扬弃继承”基础上的“移步”,加快实施“转化创新”意义中的“换形”,从而创作出与当代社会、当代都市、当代剧场、当代审美相适应的新的一代戏曲。